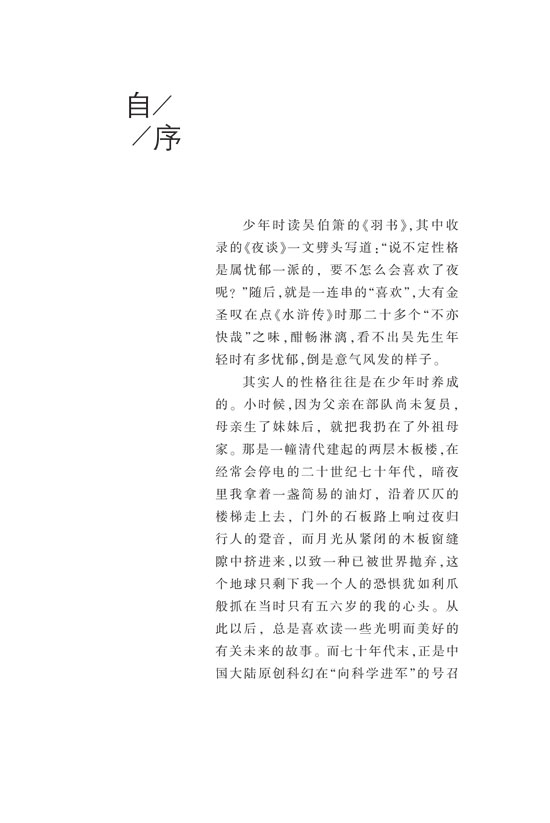图书简介
这是著名跨界作家燕垒生的一部科幻作品选集,包括《瘟疫》《礼物》《铁血年代》《天人永生》四部中短篇科幻作品,其中《瘟疫》获得过科幻银河奖读者提名奖,并改编为话剧《我想我疯了》。选取的作品背景均设定在未来世界,作者用朴实简练的语言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勾画出末世之际人类进入全面危机时的情形,构思新颖独特又巧妙缜密,表现出强烈的个人风格,同时寄寓了作者对生活和世界的深入思考。
作者简介
燕垒生,本名张健,20世纪70年代生人,浙江桐乡人。总角发蒙,弱冠操觚,而立付梓,作品多为幻想类文字。作品有“天行健”系列、《贞观幽明谭》、“道者无心”系列、《西域幻沙录》、《猫梦街》、《燕垒斋诗词钞》等。
编辑推荐
这是四个有关绝境的故事。
灾难降临,一无所有的小人物在底层挣扎着求生,当所有希望都已成为绝望,当所有前途都已成为尽头,只要心底的光明不灭,就仍要向前走。
燕垒生是架构故事的高手,面对末世,危急时刻,人性的冲突,人与环境的冲突,人类极致情感的表达,均通过两难的绝境和令人信服的细节得到充分的展现,在带来强烈阅读快感同时,使读者的精神得到升华。
书摘
我知道我是疯了,一定是。没有一个人会自愿做这种事的。
每天我穿好从头到脚的防护衣,在我心中并没有一点对此的厌恶和不安。相反,很平静。一个正常的人不会如此平静,即使注定你会死,在做这些事时总会有什么想法的。可是我每天把一车车的尸体像垃圾一样扔进焚化炉里,却像这事有种趣味。
我知道我准是个疯子。
瘟疫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
当第一个病例被披露时,人们还没有想到这事的严重性,有一些愚蠢的生物学家甚至欢呼终于找到了另一种生命形式,因为引起这场瘟疫的那种病毒的分子链中是硅和氢、氧结合而不是碳。
当感染这种病毒的初期,除了全身关节稍有点不灵便,并没有什么不适。然而到了两周后,病人会突然不会动了,首先全身皮肤成为二氧化硅,也就是石头。但此时人并没有死,眼睛还能眨动。这时的人如果想强行运动,是可以动的,只是皮肤会像蜡质一样碎裂。我看到过好几具石化了的尸体,身上凹凸不平,全是血迹。随后内脏也开始石化,直到第六周,全身彻底石化。换句话说,到第四十天左右,一个活人就成为一座石像。
没有人知道这种病毒是如何产生的。现有的抗生素也只能对蛋白质构成的病毒起作用,对这种病毒毫无用处。
更可怕的是,这种病毒的传染性极大,甚至从呼吸也可以传染。而初起阶段,正因为没有症状,极难发现。你可能在人群中走过,就已经被感染了。
唯一的特效药是酒精。
酒精可以延缓这种病毒的活动,但充其量不过是让病毒的代谢延缓一周。即使你浸在酒精里,也不过多活一个星期。据科学家说,人体的石化,是因为病毒的代谢物堆积在细胞里。酒精其实不是杀死病毒,而是让病毒保持活性。所以,酒精不是药,而更像一剂毒品。通俗点说,因为病毒保持活性,它们活得时间更长,在体内同时生存的个体数就更多,因此在它们代谢时产生的尸体也就更多,到后期人体石化得更快。
可不管从哪方面来说,人们觉得酒精还是一种灵药。
酒精的消费量呈几何级数增长。
当然,统计局早已经撤销了。世界也没有国家可言。在瘟疫早期,一些侥幸没有发现这种病毒的国家还在幸灾乐祸地指摘是其他国家的国体以至于造成了这场瘟疫,而传到自己国家时又气势汹汹地指责别国采取的措施不力。然而当这种瘟疫已呈燎原之势时,谁也说不出多余的话了。不管意识形态如何,国体如何,在这场瘟疫面前人人平等。
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世界大同,实在是种很奇妙的现象。
紧急应变机构建立了。而这种应变,只有一种对策。对感染的人进行隔离,未感染的人发防毒面具。好在这种病毒的个体尚通不过石墨过滤器,不然人类真的要无处可逃了。
当一个人被发现感染了病毒,立刻被收缴面具。因为对于尚未感染的人类来说,一个带菌者无异于一头危险的猛兽。这些人立刻被抛弃在外,有钱的开始酗酒,不管会不会喝。没钱的到处抢劫。事实上也不必抢劫,因为三分之二的住宅已经空了,随便进出,财物也随便取用。
我的任务是善后工作。说白了,就是到处收集已经变成石像的尸体,运到郊外焚烧。由于没有药,所以只能如此做,尽量把病毒消灭掉。做这事,不但感染的可能性更高,更可怕的是,我们往往收集到尚未彻底石化的尸体。而把这样的尸体投进焚尸炉,往往会从里面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我有两个同僚因为不能忍受良心的谴责而自杀了。
这不是个好工作,但总要有人做。
我说我疯了是因为我不但不害怕这种惨叫,反而在投入每一个石像时,总是满心希望它发出那一声绝望的呼叫。
毕竟,不是所有的石像都是门农。
我驾着大卡车驶过空荡荡的街道。今天只收了七具尸体,每一具都不像还会在焚尸炉里叫唤的。
驶过一个幼儿园时,我看见一个没戴面具的男人抱着一堆东西从里面跑出来。
由于儿童的身体小,他们感染病毒后发作得比成人快得多,因此早就没有儿童了。然而这幼儿园门口并没有表明无人的白标牌,也没有红标牌,说明里面还有正常人。
现在,无人住宅钉着白标牌,而病人住宅则是红标牌。这是紧急应变司制定的制度,便于让人一目了然。如果病人抢劫的是无人住宅,并不违法。而他从这幼儿园里出来,就算那里没人了,他也是犯了抢劫罪,我可以将他就地正法。
我跳下车,拔出枪来,对他喊道:“站住。”
他站住了,看着我。他的手里,是一堆女人的衣服。不知道他拿些女人的衣服做什么,也许市区那家百货公司已被人翻得差不多了吧。
我用枪对着他,背书一样地说:“这不是无人住宅,你已经触犯《紧急状态法》第八条,必须接受死刑。”
这些话我已经说了好多遍,已是熟极而流,用不着再背诵了。在这样的年代,如果没有严厉的法律约束,那么这个世界一定比地狱还不如。
那个男人的脸也挤作一团。能做这样表情的人,至少还可以到处跑上一个礼拜。他道:“我不知道,我是新来的。”
“不必解释了,你必须接受处罚。”我冷冷地说。这些理由我同样听过好多遍,他们为什么不编个新鲜一点的理由呢?尽管他必须死,可他在临死前,能让我听到一句新鲜的话也好。
他的脸扭曲、变形,嘴里开始不干不净地骂着。我开了枪。在枪声中,他的脑袋像是一堆腐败的烂肉,四处飞溅,在墙上形成一个放射状的痕迹。而他的尸体,也是真正的有血有肉的尸体,向后倒去。
《紧急状态法》第八条,凡病人进入未感染者住宅,不论何种理由,一律就地处决。
这条不近人情的法律得到了所有未感染者的支持,因而得以通过。
跨过那具尸首,我踏进那个幼儿园里。
生与死,在这个年代已不重要了。杀了一个人,我心中没有一点波动。我想的只是,他进入这里,可能原先的住民已经死了,或者这里的住民已被感染。不论如何,我必须要弄清楚。
“有人吗?”
我喊着。在教室里,还贴着一张张稚拙的儿童画,《我的家》《纸飞机》……在那些夸张得可笑的人和景中,依然看得到画画儿的孩子的天真和可爱。尽管画笔拙劣,但至少看得出画里的人还有着柔软的四肢和身体。
我没有孩子,连女友也没有过。
我伸手触摸着那些画。陈旧的纸张,已经有些泛黄,落满了灰尘,尽管隔着一层手套,我还是感觉得到那些纸在我的触摸下发出干硬的“窣窣”的声响。
没有一个人。黑板上还写着“一只手,一口米”这样的字,也已经淡得几乎看不清了,但这里没有一点有人迹的样子。也许这真是个无人住宅,我是错杀了那个人了。
可是我没有一点内疚。也没什么好内疚的,他无非早死几个星期而已。也许,对于他来说,早几个星期结束痛苦并不是件坏事。
我穿过了几个教室。后面是一排宿舍,但没有人。看来是个无人区了。我的车里还有几块标牌,得给这儿钉上块白标牌了,省得再有人被我错杀。
我想着,正准备走出去,忽然在楼道下传来了一点响动。
楼道下,本是一间杂物间,没有人。从那里会传来什么?目前已没有老鼠了。所有的老鼠早于人石化,因为个体要小得多。现在,只有大象才能在感染后活得最久。
我打开杂物间的门,看到那里还有一扇门。这门是通向楼下的。
这里有个地下室!我推了推门,门没开。
我退了一步,狠踹了一脚,“砰”一声,门被我踹开了。
下面,简直是个玩具工场。
我说那像个玩具工场,因为足足有三十个小孩的石像。有各种姿态,甚至有坐在痰盂上的。但那确实都早已石化了。
我苦笑了一下。每个小孩,也有近六十斤,三十多个,一共一千八百多斤。这可是个体力活。我抱起一个手里还抓着玩具汽车的小男孩,扛在肩上,准备走出这间地下室。
“你不能带走他们。”
我看到从墙上一个隐藏得很好的门里走出一个人来。听声音,那是个女子,身上还穿着厚重的防护服。
我站住了:“还有人?你刚才为什么不出来?”
她盯着我隐藏在面具后的脸,像要看透我脸上的卑鄙和无耻。她慢慢地回答说:“你是乌鸦?”
我不由苦笑。“乌鸦”是一般人对我们的俚称,因为我们的防护衣是黑色而不是一般的白色,而做的事也像报丧的乌鸦一样。
“算是吧。”
“你要把他们带走?”
我看看手里抱着的那个像个大玩偶一样的石像,道:“这可不是工艺品。”
“你要把他们烧掉?”
“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请与紧急应变司联系,电话是010-8894……”
“我不是与你说这些,”她有点恼怒地说,“你不能带走他们。”
“小姐,”我说,“请你不要感情用事。古人说壮士断腕,也是这个道理。他们已经没有生命,如同一颗定时炸弹一样危险,你把他们藏在这儿,能够保证你自己不会染上吗?”
她愤怒地说:“不对,他们没有死。”
我有点好笑。这种感情至上主义者我也碰到过不少,如果由着他们乱来,人类的灭绝那早就指日可待了。我说:“一个人已经成为石像了,你说他没有死?”
她说:“是。他们并没有死,只不过成为另一个形式的生命。就像我们人类的身体里,纤维素极少,但不能由此说绝大部分是纤维素构成的植物不是生命一样。”
我有点生气了。她真如此不可理喻吗?尽管政府告诉我们,如果遇上人无理取闹,可以采用极端手段,但我实在不想拔出枪来。我耐下性子,努力让自己温和地说:“小姐,你说他们有生命,那他们有生命运动吗?植物不会动,可还会生长。”
她说:“他们会动,只不过他们成为这种形式的生命,时间观念与我们不同了。我们的一秒钟,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天,一个月,一年。但不能因为他们动得缓慢,我们就剥夺他们的生存权利。”
我笑了:“小姐,科学家们早就证明了,人一旦石化,就不再有生命了,和公园里那些艺术品没什么不同。小姐,你想成为罗浮宫里的收藏品,机会有的是。”
她尖叫着:“他们骗人!”她拉着我的手,说:“来,我给你看证据。”
透过厚厚的手套,我感到她的手柔软,却又有些坚硬。我吃了一惊,说:“你已经感染了?”
她苦笑了一下:“是,已经有些日子了。根据一般人的感染速度,我大概还能活上五天,所以我一定要你来看看。”
她给我看的是那个坐在痰盂上的小女孩。这小女孩脸上带着一种奇怪的表情,我也并不陌生。每一个人大便后都是这样的,不论年纪大小。然而她的手提着裙子,屁股却不是坐在痰盂上的。
她说:“这个孩子已经石化两年了。两年前,在她还没完全石化时,是坐在痰盂上的,可今天她却成了这个样子。你说她想干什么?”
我说:“天啊,她想站起来!”
她没有看我,只是说:“是。她知道自己拉完了,该站起来了。只不过时间对于她来说慢了很多,在她思想中,可能这两年不过是她坐在痰盂上的一小会儿,她甚至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的动作对于她来说太快了,快得什么也看不到。你把她扔到焚尸炉里,她被焚烧时的痛苦甚至还来不及从神经末梢传到大脑就已经成为沙子了。你说,你是不是在杀人?”
我只觉头有点晕。根据统计,我一天大约焚烧二百个人。照这样计算,两年来,七百多天,我是杀了十四万个人了?
也许她在说谎?然而我不太相信。因为石化不是快如闪电,从能运动到不能运动的临界时间,大约是三十分钟。我见过不少人在这三十分钟里强行运动而使本来的皮肤皲裂的例子,有些收来的石化后的尸体皮肤几乎像鱼鳞一样。也就是说,这小女孩不可能在三十分钟里保持撅着屁股的姿势一动不动的,不然她的皮肤一定会裂开。然而现在她的皮肤光滑无瑕,几乎可以当镜子照。
可是,要我相信一个变成石头的人还能动,还能思想,而思想比血肉之躯时慢上千百万倍,这难以让我想象。我不是知识分子,不会相信别人口头的话,即使那非常可信,非常诱人。我也只相信我看到的。
我的手摸向枪套。对于不想理解的事,枪声是最好的回答。
我的手摸着枪把,却没有拔出来。那支枪像有千钧重量,我的手只是按在枪套上,没有再动。
我看到了她的眼睛。她的眼神在防护面具后面是一种怜悯和不屈,仿佛我只是一只肮脏的爬虫。
我移开了目光,道:“把你的防护衣脱下来,你已没有资格穿了。”
第二天上午,我在一个兵营里收到了一大堆士兵。在回去时,我到那个幼儿园里转了转。
她正在晾晒衣服。现在她不在躲闪,也许没这个必要了吧。阳光很好,她在晾晒衣服时,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我把车停在门口,在边上抓了一包食物,向她走去。
她看见了我,停下手里的动作。我站在她身边,把那包食物递过去。
“你来做什么?”她的目光还是不太友好。
“你没有粮食配给,我给你拿来一些。”
粮食配给也是紧急应变司的一项措施。由于植物与动物一样,同样会石化,因此食物极为稀少,每个正常人每月只有十八千克的食品。像我们这一类乌鸦,由于没人肯干,因此每月要多十千克。感染者立即停止配给食物,让他们自生自灭。
她看着我:“是怜悯?”我也看了看她,但很快不敢面对她的目光:“是尊重。”
她道:“如果你真这么想,我只希望你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
“当我石化以后,不要把那些孩子烧掉。”
我抬起眼,看着她眼里的期待,实在不忍心告诉她真话。我垂下眼睑,道:“好的,我答应你。”
我无法告诉她,我的任务就是收集已经石化的人体,然后烧掉,不论他们是不是成为另一种生命形式,是不是还有感觉。然而我只能说些这种话,让她在剩下的时间里得到一点不切实际的安慰吧。
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把自己宝贵的食物给她,那也许是太蠢了。可是我总觉得我应该这么做。不能要求我成为殉道者,那么我只能做一个旁观者。
书评
幽邃玄秘,奇诡绮丽,燕大叔的文字,总带着一丝来自上古的清寒。
——知名作家、人民文学奖及银河奖得主马伯庸
燕垒生的作品,有一种透过时间和心灵的特殊魅力。那是时间的沧桑感和心灵的震撼力,成为其不可代替的特色。尤其是《瘟疫》一文,给予我极大的震撼。一个个石化的逝者,是否仍然有另一种形式的生命,不为世人所理解?这不仅是怪诞的想象,也包含着一种深刻的哲理和伦理观念。这就是燕垒生,一个杰出的幻想家,毋宁说是独行的思考者。
——新中国第一代科幻作家、著名科普作家刘兴诗
燕垒生是个奇特的作者,他既有上世纪80年代的科幻作家的那种古朴老成,又有新世纪科幻作者的前卫和灵动。这使得他的小说在叙事上显得格外老练成熟,引人入胜。
——资深科幻编辑刘维佳
版权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