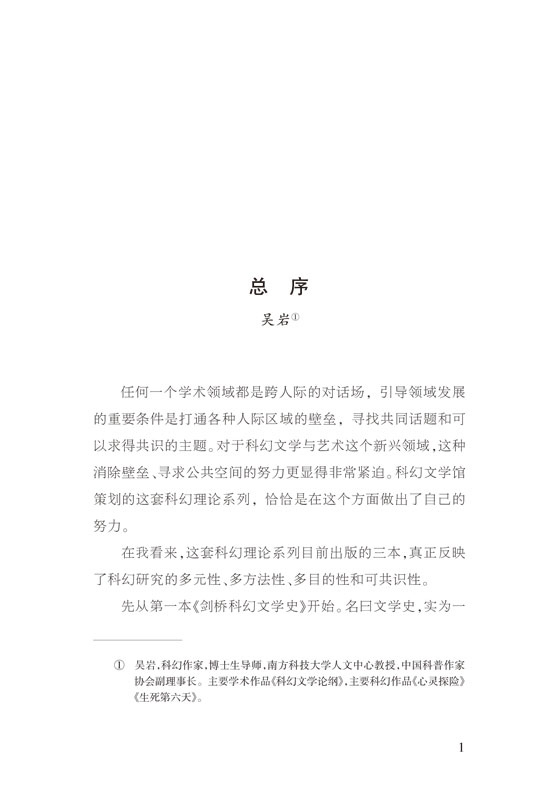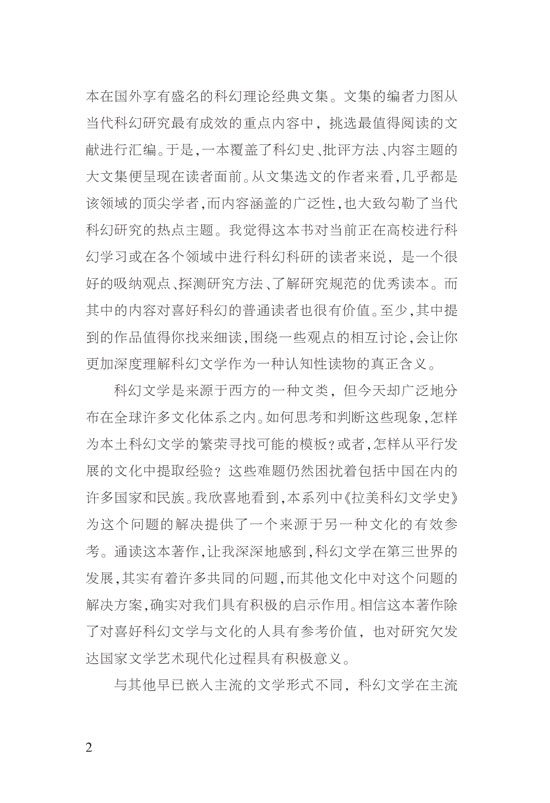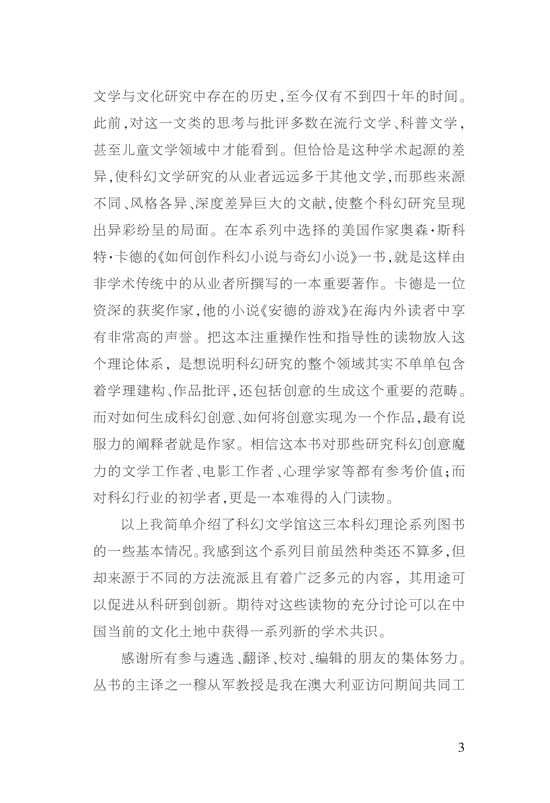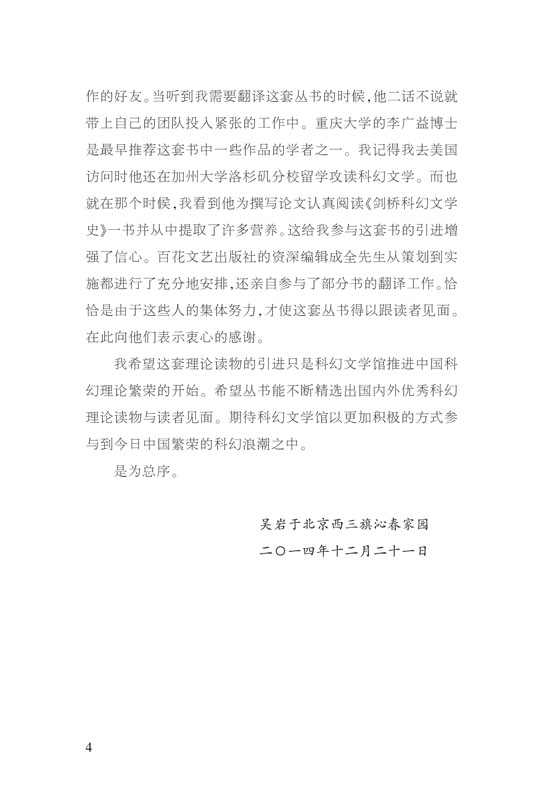图书简介
本书分为历史篇、批判方法及科幻分支流派和主题三部分。
第一部分在介绍了科幻的特点之后,主要追溯了从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直到现在的科幻发展历史,其中包括电影、电视等相关章节。
第二部分介绍了研究科幻的四种主要批判方法,它们的理论基础分别是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和酷儿理论。
第三部分是主体部分,介绍了科幻的各种主题及其分支流派,包括科幻与生命科学、硬科幻、太空歌剧、历史演义小说、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等。
作者简介
爱德华•詹姆斯:英国雷丁大学历史学教授,2001至2003年曾在美国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历史系任职,曾发表多篇关于中世纪法国和英国的研究文章,以及有关科幻小说史的文章。
法拉•门德尔松:英国密德萨斯大学美国研究高级讲师,1997年至2003年担任科幻基地主席,2001年成为科幻基地杂志《基地》编辑,发表过多篇科幻论文和评论。
编辑推荐
《剑桥科幻文学史》(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cience Fiction)一书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于2003年12月出版,隶属于“剑桥文学与经典丛书”(Cambridge Companions to Literature and Classics)系列,由爱德华·詹姆斯和法拉·门德尔松两人主编,多位当代知名科幻文学学者和评论人合作完成,是一部融合了科幻文学历史与评论方法的集大成之作。
作为剑桥大学文学院指定教材,本书既收录了权威科幻文学研究者的真知灼见,又网罗了著名科幻小说创作者的写作心得,论述角度新颖独到,获得世界科幻文学研究及创作领域的认可。
书摘
概论:科幻小说之阅读
法拉·门德尔松
《剑桥科幻文学史》旨在向读者介绍科幻文类及其相关研究,有鉴于此,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勾勒科幻历史,讨论主要作家、编辑以及形成科幻文学结构的人和市场力量;第二部分有关科幻批评研究方法;第三部分是论文集,这些论文探讨了评论家和作家公认的科幻本质问题。本书作者的母语都是英语,因而,所涉皆为主导了二十世纪科幻的英语科幻小说。
我们之所以对本书结构作出这样的安排,是因为我们相信读者非常了解科幻的内容,也清楚本书作者有着同样的研究水准,关于第二点大家可能会有些争议。事实上,科幻本身一直就处在争论之中,它的某些情节特点和比喻还有待人们进一步认识。本书的文章常常互为参考,有些是活跃在评论界的学者撰写的(我们尽可能多地反映这一类),有些则是支撑科幻市场的科幻迷撰写的。一般来说,读者都期待看到科幻小说描述的事件发生过程,而不是事件结果,当然,他们在阅读过程中也会用到相关批评工具,可这些批评性工具本身也是有争议的,因为在科幻领域科幻迷派别各异,评论家也是山头林立。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可能有些人会觉得主题性论文数量过多,还有些人会不同意某些论文中认为科幻出现于二十世纪的观点,他们倾向于把时间推到十九世纪或者更早。这些不同意见本质上还是源于科幻,因为文学和读者的标准及要求迥然有异,导致科幻写作模式大相径庭。尽管科幻电影场场爆满,但科幻文学却并不普及。此外,本书没有收录具体的文本分析,因为是讨论,收录“有代表性”的论文会适得其反,而且,太多的文章用科幻佳作来粉饰,不难发现某些论文中一些名词反复出现,我们的原则是只有围绕某一主题或模式的具体准则出现时,我们才会进行持续的文本分析。
不过,理解科幻的最佳途径就是把本书中许多评论家提出的理论和范文结合起来阅读。过去有关科幻特点的观点主要基于科幻经典小说,说法笼统,近来不时受到挑战,人们迅速发现那些文章大多数只能满足三分之二的科幻理论需求,因此,本书就用当代最佳作家之一格雷格·伊根的《希尔德之梯》(Schild's Ladder)(2002)来考察那些科幻理论。《希尔德之梯》是一部硬科幻太空歌剧,因为它本身含有科幻历史和批评话语思想,所以它对科幻的理论提出了质疑。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个让大家困扰不已的观点,即科幻是一种讨论或模式,而不是一种文类。
如果科幻是一种文类,我们就可以随便拿起一本书轻松了解它的梗概了。譬如神秘小说,就一定会有某些东西等待发现;浪漫故事,就一定有两人相遇,发生冲突,然后恋爱;恐怖故事则会讲述某非正常物体的入侵,但最终会被驯服或者消灭。伊根的《希尔德之梯》兼具上述三种模式,小说中科学家卡斯极力证明萨鲁姆帕特(Sarumpaet)数学方程能够成立,多年以后,奇卡亚则饶有兴致地探求起卡斯试验不能成立。如果说这还不足以称为神秘小说,那就很有必要探寻谁是破坏太空空间站林德勒(Rindler)的人,可立马就有人说这样的小说属于“惊悚体”。其实,这些情节本身就令人恐怖。小说中的主人公吞噬了地球之后,他还能忍住消灭新宇宙吗?当然,这是科幻小说不是电影,所以不一定非要来个好莱坞式的大团圆结局,这在科幻作品中十分普遍,例如,史蒂芬·巴克斯特和约翰·巴恩斯也都是以刻画人类大毁灭而著称的作家。小说最后是奇卡亚和马里亚玛之间的浪漫爱情故事:青梅竹马的心上人分离了近七百年,这样的爱情故事在许多小说里面可能都是核心内容,不过,在科幻中这样的爱情故事写法大异其趣,后面我还要详加说明。
正是因为科幻小说乐于从其他类型小说中汲取情节结构,所以人们常常很难把这些小说归类于科幻。那么,科幻小说自己的叙事模式到底是什么样的呢?目前好像还没有确切的说法。不过,如果说是最具科幻小说特色的东西,那就是“惊异感”了。
惊异感是科幻小说的情感核心,大卫·奈叶曾说这种反应是对神奇的赞叹,自然如土星的光环,人工如空间站或者火箭船等(见本书本第二章格温妮丝·琼斯所撰章节)。在科幻小说发展的前十五年(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起),美国杂志中大部分故事如杂志标题《惊奇故事》(Amazing)《惊异》《惊悚奇迹》(Thrilling Wonder)一样都含有惊异等字样。最早的科幻小说主要依赖新发明创造,或者到达一个新的地方,那个时候读者读到这些就够了;他们可以站着凝视飞行的城市,或者惊诧于超级武器的威力。小说以描述性为主,由不熟悉环境的主人公向读者进行讲述,或者以读者的名义旁听某个讲座。几乎所有的故事结局都是宇宙和平,或者某项发明和发明家遭到毁灭,之所以结局安排成这样,是因为作家也无法超越时代的局限,因而只能使用类似于“醒来是一场梦”的手法,也许目的就是为了避免结局感。约翰·克卢特认为秘密在于:
史密斯博士和他同时代的作家A.E.范·沃格特踽踽而行,他们也许热爱构思未来,但同时他们又明显表现出对预示“真实”未来的东西有一种深深的不信任和恐惧,这种未来就是我们幼年时期的突变。“透镜人”(Lensmen)系列和其他优秀小说一样是逃避主义,我们因逃避主义而爱上那个系列,但它并未逃避1930年,而是逃避未来。
结果是惊异感和表现主义的结合,惊异感这一核心让科幻继续壮大。《希尔德之梯》前35页是独立的,讲的是一个经典的小故事,可视作科幻早期成就,展示了惊异感在构建科幻小说内容的基本功能。在小说中,卡斯为了理论把思想装入自己高约两毫米的躯体内,它可以远达距离地球三百七十光年的地方。这个故事情节非常简单,卡斯寻求外星人的帮助测试萨鲁姆帕特数学原理在深层空间的安全证据。外星人比地球人年长,也更聪明,他们非常谨慎,把实验分解成十五个小实验。当最终整个实验得以实施的时候,还是出了错,最后的爆炸吞没了宇宙,“短篇故事”戛然而止。早期传统的科幻中就有惊异感(数学上的概率)、智能外星人(不过在此称后人类)、盲目乐观、冷漠的宇宙方程式等,传统的科幻替代了神灵的惩罚物,扼制了人类的智慧精巧。为使读者不致厌倦,一些小的惊异点如卡斯缩小的身高、靠光生活的身体和空间站本身不时在小说中出现。
当然,我推荐《希尔德之梯》还有其他理由。科幻小说不是静止不变的,诚如奈叶所言,惊异感是非常脆弱的,熟悉了就很难再称为惊异。尽管过段时间更大更好更复杂的发明和符号又可以出现,但厌倦无聊常常使人反胃。《希尔德之梯》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准确地把惊异感和其他文学结构结合了起来,形成了惊异感之上的科幻小说模式。首先就是伊斯特万·西克瑟瑞·荣莱(Istvan Csicsery-Ronay)所称的“荒诞不经(grotesque)”,但我们想到的是“结局”。惊异感让人们惊叹蘑菇云的美,荒诞感则让读者和作者考虑到后果。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以来,部分由于编辑奥林·特里梅因(F. Orlin Tremaine)和约翰·坎贝尔的努力(见本书第二章和第六章),科幻开始转向对结局的考虑,这一转向在《希尔德之梯》第二部分开篇有明确标记,即“要是……该怎么办”【达科·苏恩文称此为新元素】,这一思想实验对科幻至关重要,由此产生了科幻小说最流行的代名词:推测小说。从此,科幻小说大部分从当代文学中分离了出来,“思想”成为科幻小说的主角。
《希尔德之梯》以思想实验开场,主要检测萨鲁姆帕特理论,推动故事发展的似乎就是实验的结果。但是,贯穿整个小说的思想实验也产生了一些暗喻,物理成了打开宇宙之门的撬棍,保存智力和性格的密码,而宇宙、智力和性格本身就有一种崇高之美。《希尔德之梯》中的一个数字化人物这样讲道:“十岁时,我送给心上人一组投影,能将四维的旋转组转化为三球体主束”(97页)。(她喜欢那些东西。)所有这些特点都来自于“要是……该怎么办”,也就是说,解放自我、脱离肉体现实的后果是什么?实际上,这个实验比初始威胁毁灭宇宙的实验更具有挑战性。这种结构就是科幻经典的双重威胁,思想实验套着思想实验,迫使读者关注历险、神秘或者爱情故事的背景。尽管许多科幻小说的原动力依赖某个具体的科学问题,但其结构和形式与背景是融为一体的。这是因为虽然第一个思想实验可能会有崇高感,但正是隐含的“要是……该怎么办”和初始思想实验的结合,才产生了达科·苏恩文所说的认知疏离,“情节的认知核心共同决定了小说疏离本身”。
认知疏离与科幻的编码性质如风格、词汇和嵌入有着天然联系,认知疏离是这样一种感觉,即小说世界的事物和读者的经验世界不相一致,表面上是时间、空间和技术场景的变换产生了这种差异,如果真是这样,小说作品会陷入说教和过度白描。早期科幻共同使用的技巧被贬为“信息倾销”(info-dump),小说中的人物向他的听众们介绍他们应该知道但读者却不清楚的事,这种方法很难避免,就在批评性观点获胜、概念突破的时候,整个世界变得超乎我们的想象,这是作者传递信息的唯一工具。即使在《希尔德之梯》中伊根也无法避免,萨鲁姆帕特理论最终被推翻,伊根不得不让一个角色作长达两页纸的公开演讲(88页到89页)。为缓和这种说教,作家有意识安排主角不熟悉材料,并把说教作为代表新理论“宽容”的托词,同时假定部分读者感到烦躁不安,这虽然带有诱导性质,但是在安排上还是比较巧妙的。
细节传递信息效果最佳。七十年来,科幻作家研制出了一套工具,不会使用这套工作就说明是外行(当然,也有专业作家自称发明了一种新文类,或者强烈反对科幻的分类)。新手能很快注意到也是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科幻使用的语言,诚如格温妮丝·琼斯所言(第二章):“阅读科幻故事常常是一个比较活跃的转换过程”。
科幻中的语言并不一定可信,暗喻有时就是它的字面意义。小说“他把他的手给了她”或者“他翻了个身”会在科幻读者脑海中引起无限遐想,也许是可拆卸的身体部件,抑或是电子植入。此外,科幻作者也会通过故意构建新的技术隐喻来形成疏离感。比如,“港口的天色就像没有节目的电视机,处处闪着雪花”。不过,人们还是期望按字面意义来理解文字。不管是这样一句话,“他看到一片没有消化的牛肉,上面还留有最后一位居住者的毛发和肌肉组织”(《希尔德之梯》第三十五页),还是生造的一个词如“Qusp”。制造不和谐的效果的主要基础是:读者或者会理解所写内容,或者会创造意义来弥补缺失的信息。这两个技巧对科幻十分关键,而且它们是交叉叠加的,科幻主要依赖词汇、结构和一套深深嵌入这种文类的共同思想的演化。例如,过去描述星际舰队长距离穿越需要好几页纸,现在只要简单提到“FTL”(比光速快)就可以说明问题了,这种对科学成果的利用是硬科幻的标志之一(参见第十三章凯瑟琳·克莱默所撰内容)。不过,科幻也有自己的隐喻,例如,勒古恩在《一无所有》(The Dispossessed)的开头这样写道:“有一面墙,看起来并不重要……即使一个孩子也可以轻松攀越……那是思想之界。然而,思想是真实的……墙内的东西和墙外的东西取决于你在墙的哪一侧。”作为科幻读者,我们很清楚小说中的墙既是指探险的障碍,同时也是一种叙事隐喻,因此,勒古恩在小说的开头前五行就为我们创造了疏离和故事。
伊根还运用过去科幻小说中的概念来表达意义,将信息一点一点释放到他创造的世界之中。雅恩是个非肉身科学家,非肉身概念在威廉·吉布森[7]和弗诺·文奇的“传统文本”(legacy texts’)中就有提到,他可以“随时将宇宙舰队调到林德勒空间站,在数百万吨副产品产生之前,宣布他们来拯救宇宙”(《希尔德之梯》第五十二页)。虽然我们清楚我们应该了解非肉身概念的意义,但可能理解得并不到位。伊根的小说还提到了海因莱因(Heinlein)和其他作家的聚变火炬舰队,有关人体冷冻的假设,以及约翰·坎贝尔《惊异科幻》培养出来的地球霸权小说中的内容。宇宙科幻史可以一言以蔽之,但宇宙舰队再用五十页纸也难以说清楚,我们必须想办法作进一步探讨。
然而,我们也有被嘲弄的感觉,因为宇宙舰队本身就是科幻的一个传统,约翰·克卢特在本书第四章这样说道,“可换过去概念的运用可以显示风格,但并不一定要做实质上的提倡”。宇宙舰队为性和性别冲突思想所困,从一个星球到另一个星球寻找“未来核心故事”(本书第四章),由此说明叙事方式并无多大变化。伊根的宇宙舰队概括了小詹姆斯·提普垂的观点,即那些声称保护我们的人经常以他们自己为摹本来虚构侵略者(参见第八章沃罗妮卡·郝琳杰所撰内容)。小说中的齐卡亚父亲年轻时也曾迷茫并且擅长撒谎,宇宙舰队在遇到他之前,已遭到人类后代的嘲弄,他们给宇宙舰队讲自玛格丽特·米德时代起就用来愚弄人类学家的那类故事。在小说中,宇宙舰队还有一个功能就是用来挖苦科幻评论家,那些人因为某一本科幻小说和他们的政治观点相左就对其进行无端指责,当然,这样的人不限于政治左派。
伊根除了用传统文本对他创造的世界进行分层以外,还创造了他自己的嵌入法。谁是宇宙舰队?他们是什么意思?我们逐步获得线索得以理解,真正突破性的理解是在宇宙舰队讲述他们的动机的时候,而传统的写法往往是反派人物集中出现的时候。不过,伊根设法把我们和我们对小说主要角色的猜测分离开来,就好像猜测的那些人并不是我们。小说的主人公卡斯再造时直径仅两毫米,“密封在真空瓶中,以光为食”(《希尔德之梯》第五页),不过,身体转移的概念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因为现代科幻小说中的主角大家都很熟悉,他们一般在自己的宇宙中能力超强,这都无须向我们解释,我们也不觉得有任何解释的必要。这些人对“自我”有不同的认识,他们为了边界问题不停地协商,“当有办法马上不费力地把你自己转换成别的东西时,你要保持身份的唯一渠道是划定自己的边界。但是,一旦你错失良机,你则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只能成为智人”(《希尔德之梯》第六页)。这条界线就此尘埃落定,那些人就不再是人类了。但是,我们对身体的文化理解并不是单一的,当然他们也不是,有些后人类选择生而具有的身体,有些则选择活跃的备件,还有的后人类认为备件只有在死亡时才有意义,更有许多人选择数字化的生活,身体的存在只是为了实现某种互动。因为在这种文化中,存在的方式不同,所以死亡的意义也千差万别。
他们也不像人类一样有性别之分。伊根沿用女权主义作家传统,保留了性别,但把性别和身体剥离开来,非常有意思的是,小说中男女性姓名都是以元音结尾的,这点有悖于西方传统习惯,这种不一致从下面这段倒叙的结尾部分可窥一斑。
他两腿间的皮肤红红的,有肿块……触摸有痒感……他还会改变想法和情感。一切都是自愿的,他父亲说,除非你深深地爱上某个人,并且那个人对你也有好感,否则,你们无法做爱……那些夫妻只能那样,这就像每对夫妻都有一个不同的孩子。(第77至第78页)
在这个阶段,故事听起来就像父母为保护孩子而讲的神话,最后的揭晓必须等到齐卡亚被拉司马带到床上。
“噢,瞧我们干的!我知道那一定很美妙,我想我有适合这里的东西,绝配。在这里,也许甚至……就这里!”
齐卡亚咬紧牙关,但他无法阻止她的手指在他身上四处游走,一个以前从没有人碰过的地方被人触摸,而且甚至你自己都没有见过或触碰过,这是一件多么要命的事。
自然从不想象,只是人们总会找到新的办法把它们联系起来。(第161至第162页)
但是,选择谁来联系?这种联系为什么不稳定?在小说的第一节,卡斯动摇了,因为她的肉身使她认识到性是最亲密的行为,但拉因兹却不这样认为,他是主动和她分享宇宙的。这时我们得考虑“性别”或者如第十章温迪·皮尔森所说的“酷儿”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两性身体构件相同,都能体验彼此的感受,性别更多的是肉体和非肉体的区别,而不是男性和女性的区别,那就绝对可以说《希尔德之梯》的整个人类话语都是酷儿。
他们是和我们完全不同的生物,只是没有明确罢了,诚如詹姆斯·冈恩在(前言)中指出的那样,正是分层、嵌入和特有的素描把科幻小说从说教当中拯救了出来,但说教并不完全是负面的,它也不是科幻独有的,只不过科幻更有意识地使用了它,正是这一基本技巧把科幻的叙事风格导向当代小说读者并不熟悉的方向。伊根为避免说教,把虚构的世界搬到了中心舞台,主流小说作家并不指望这样描写会有什么特点,但科幻作家通过认知疏离讲出了很好的故事(见本书第十、十一章有关内容)。由此我们再来看科幻的另一个特点,早期科幻多误把古灵精怪作为故事场景,但有些作家则成功地将地点提升到了人物层次,他们做的直截了当,例如,墨里·莱因斯特的《孤独的星球》(The Lonely Planet)和朱迪斯·墨菲的《彭特拉》(Pennterra,1987)都让星球有了生命。但更根本的是星球产生趣味性的方式,其故事对人们的生活方式至关重要,勒古恩的《黑暗的左手》(The Left Hand of Darkness,1969)和《一无所有》(1974)与金·斯坦利·罗宾森的“火星三部曲”一样都把政治制度和地形联系了起来。布赖恩·奥尔迪斯的“赫星纪元”(Helliconia)三部曲是这方面的杰作,生活在赫利康尼亚星球上的生物只是作为故事的生态面而存在,而主角则是星球。《希尔德之梯》中这一成分的出现比较晚,空间站虽然吸引人,但缺乏想象,而在另一方面,光明、带有温德克斯(vendeks)和气流花的真空调节器则吸引了读者和故事主人公的感官,甫一发现,小说的性质就发生了惊人的跳跃,再一次强化了科幻与主流文学的区别。
光明是齐卡亚和玛利亚马发现的,当时他们一起被困在太空舱,玛利亚马的“Qusp”,即储存的个性被嵌入了齐卡亚的肾脏。科幻喜欢把浪漫爱情和内脏扯在一起,因为在人的体内活动无疑是离那人最近的了。当然,科幻也喜欢模棱两可和空灵,没有身体就谈不上性,科幻是少有的几种文体把亲密关系处理成临界状态的,雅恩就因为相关神经太过粗糙无法正常对待性。性可以表示友谊和团体,但却不代表浪漫爱情,齐卡亚和玛利亚马不仅相互吸引,而且也为宇宙的荣耀、真正的爱情和宇宙的浪漫所吸引。也许科幻是浪漫小说真正最后的城堡,科幻的主人公常常和宏观世界陷入恋情。主流小说写到的多是人际关系的微妙,而科幻话语则往往是关于人与世界、人与宇宙的关系,主要突出伟大的事件(战争、登月、饥荒)和伟大的思想(演化、外星人接触、不朽)。《希尔德之梯》中齐卡亚和玛利亚马的爱情并不影响他们探险,但在进行宇宙探索时他们是排斥情感的,这种爱情逆转、坚持爱情外显而不是内在的观点常常为非科幻评论家所诟病,被指缺乏人物塑造和情感描写,比如,在小说发展到某个时刻时,人们一般都期望主人公投入各自的怀抱,然而科幻小说家却不屑于此,“没有什么能够堪比四千年的等待,也许原创理论除外”(第246页)或“一个宇宙的种子藏在排水沟里”。
然而,和惊异感纠结在一起的是孤独感,它和探险的快乐一样是科幻的一部分,它是冰冷的浪漫主义,爱情的目标永远不在其中。硬科幻中的“冷酷的方程式”(此处借用汤姆·戈德温的科幻故事标题)概念就是这种孤独感即冷漠宇宙的明证,那些严苛的规则而无关乎爱情决定了我们的生死,宇宙是冷傲的情人。《希尔德之梯》正是依赖了文本的科学超结构释放的寒冷:齐卡亚和玛利亚马可能爱上光明,但它是没有情感的,和任何生态一样,如果他们不能适应,必然的结果就是死亡。
科幻还把孤独视作人物的中心要素,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科幻过度使用了孤独这个概念,孤独的个人被视作天才,很少有人质疑,它其实反映的是几代书生的焦虑。虽然现在科幻中的那种自负大大减弱,但其修辞力依然不减当年,孤独在《希尔德之梯》中跟在经典科幻范·沃格特的《斯兰》(Slan)(1940)中一样举足轻重。齐卡亚和玛利亚马都认为“不同”就是优越,他们少年时,相信自己的生活就是宇宙叙事的中心,从而导致他们对发现外星人这件事秘而不宣。成年后,他们遇到重新建构的智人,这些人已经把歪曲的自我叙事发展成意识形态,他们表示愿意摧毁他者。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见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的传统已经有能力讲述新的故事,将他者融入世界。伊根在《希尔德之梯》中的部分成就就是让新世界的声音响了起来。宇宙以其依然冰冷的方程式强有力地改变着宇宙舰队,我们再次明白情节和人物比任何主角更有生命力。
科幻的话语意义复杂多样,语篇可以做多种解释,每一个解释都能生成一幅完全不同的画面,过去八十年来各种各样的学术规则和科幻迷准则就充分说明了这点。随着批评家越来越多地引用科幻迷的观点,过去科幻迷所认为的经典海因莱因、阿西莫夫(Asimov)、克拉克和学者认为的经典迪克、勒古恩、巴拉德之间很严格的分界已模糊不清。本书各个作者都从不同角度引用了伊根的小说,有的从生物猜想角度把他的小说解读为太空歌剧和硬科幻,海伦·梅里克和温迪·皮尔森则发展了伊根关于性的二元论,超越了异性恋规则。激进的学者甚至还提出了现在的概念和命名机制无法接受的性规则。根据皮尔森,酷儿理论强调流动性和阈限,而不是双重性或者多样性,故此,郝琳杰指出科幻小说创作都无法绕开女权主义。相对而言,我则认为这部小说会引起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批评家的兴趣,因为它没有受到任何生产方式和政治的影响。该书不涉任何肤色,故而可看作后人种主义小说,抑或我们可以就作品来谈谈我们的偏见(见第十九章伊丽莎白·安娜·列奥拉德)。《希尔德之梯》亦适合爱德华·詹姆斯和肯·麦克劳德(第十六和十七章),因为它的技巧性展示了形式和介绍纷争的生造情节的缺陷。甚至这本小说还可以看做历史演义小说(见第十五章),伊根讲述的不是我们的未来,他的核聚变舰队不可能来自拒绝人类空间探险的地球。最重要的是,布赖恩·斯塔布莱福特、布赖恩·艾特贝瑞、戴米安·布罗德里克和约翰·克卢特撰写的历史文章会对我们理解《希尔德之梯》及其他小说产生重要影响。科幻是在不断构建的文类,它有自己的历史,读过前面这几章,我们就会真正理解现在的科幻。
版权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