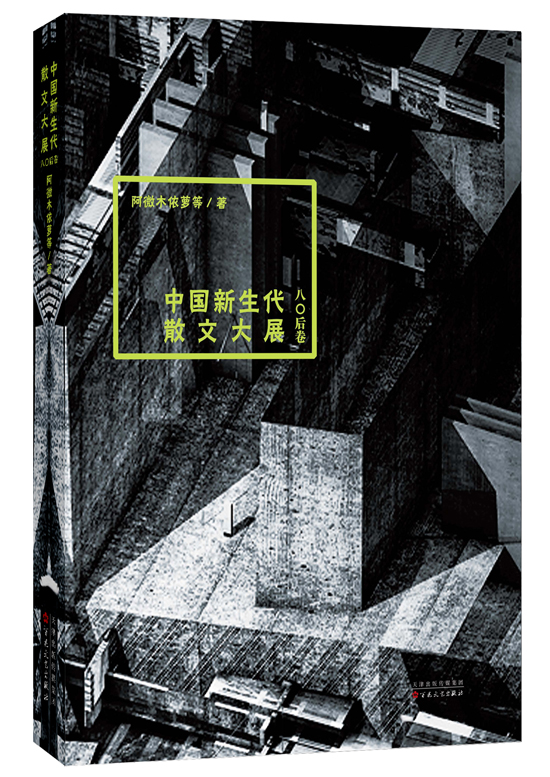图书简介
当下中国的八〇后作家,已在华语文坛崭露头角,彰显出全新的风貌与潜力。这本《新生代散文大展•八〇后卷》中收录的十二位青年作家的代表性作品,题材广泛气质各异,如同雨季中恣意生长的植物,为华语散文延伸出新鲜的可能,也展示出新生代作家锐意进取的活力。他们所追求的高远、深邃、纯粹与自由,在这些文字中清晰可触。
作者简介
本书的十二位作者均为出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青年作家,他们是:阿微木依萝、安宁、草白、陈崇正、彭剑斌、盛文强、田鑫、王选、王威廉、吴佳骏、小白、朱强。他们之中,有的已在国内文坛拥有大量粉丝,有的相对低调,但文字所及,同样才华横溢。
编辑推荐
从最初中国文坛上一个边缘化的存在,到成长为无法忽视的写作群体,八〇后作家们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的十几年间,迅速摆脱了青涩状态。在此情境下,这本《中国新生代散文大展•八〇后卷》应运而生。
之所以称之为“大展”而不称“排行榜”,乃在于我们需要更多宽阔的道路——在“比赛”与“排行”之外,道路宽阔。
闻道有先后,一批又一批新人到来,岁月因之而新。新人的到来,让时光里隐秘的接力持续进行。新人带着新的经验,新经验注定要溢出既有跑道,新经验注定是既有排行榜难以归纳的,而这正是文学接力的意义。
书摘
采玉者
尔嘎十七岁(我决定不告诉你他的真名),亚高原出生的肤质,使他差不多可以长成一个黑美的小伙子——我是说,假如他的眼睛不生病,看东西清楚并且是一对双眼皮美目,他可以初中辍学之后找到满意的工作,那样的尔嘎绝对不为生计所愁,他的长碎发飘在风中所映衬的那张脸,肯定给人黑美的感受。
你知道了,尔嘎是半瞎的人,他看东西模糊不明。
说来我已十年不见他,这位小青年的十七岁样貌在没有见到本人之前,我的想象中他是黑美的,是戴着左耳环和骑在一匹棕色马背上随时准备参加选美大赛的。
现在你可以确信,我已见到他。然而我不能保证这个人与早些时候一样好相处,他长大了,十年中我们的生活没有任何交集,天知道他有没有干过坏事,也或者因为眼睛看不清而成了极其虔诚的信徒。我断定跟他没什么共同语言,却又想见一面。
为了能在见面的时候找到一点儿共同的话题,我自然要加深记忆,回想这个人的从前。他母亲离家出走是万不能说,他父亲早亡更不能说,那么还有什么可说呢?我不知道。
然而见面的事情一点没有耽搁,是个下午,他从路那边突然走出来站在我眼前。十年不见,还是可以认出。由于见面仓促没有准备礼物,只好厚着脸皮走过去拿出做长辈的架子,高端端地喊了一声“尔嘎”。
“大姑。”他也喊我。他必须这么喊我。这称呼不代表我们是亲戚,但一个村的人都愿意攀亲带故。
“我的小侄儿,你都长这么高了。”我带出这份夸张又生硬的热情。
事实上他并没有长多高。
他站在风口上,身后的山包是枯黄的一片杂草,我的话在风声里小得听不见。他做出一个想听清楚的动作,而我却突然没了复述一遍的兴致。我们站的地方称为“干梁子”,十年了,它似乎还是十年前的风,吹起来没完没了,永远夹杂着山包上枯草和黄泥巴的味道,而这个地方没有树,只有灰尘和飞在风中的破胶纸。
我想到他的父亲。那个早亡人当年最爱领着尔嘎坐在风口上吹风。他是个喜欢吹大风的人。大风来的时候他甚至会张开双臂嘶吼,像个疯子又像个人形的老鹰。由于他这些举动至今不能从我的脑海消除,我便以为这个人没有死,只是飞走了。他走之后肯定不能随便回来,所以这些年等在风口上的尔嘎从来没有机会再见他的父亲。我猜测并且肯定他是在等待父亲,或者,至少是在这儿,他会觉得自己是个有父亲的人。想到这些我就没有勇气将他从风口处喊下来。
“风大。”
我走过去与他并肩坐着。
“风大。”
他扭头看我,回了句同样的话。
我们说完这句话沉默不言。他望着自己的脚尖,又时不时看向峡沟里卧着的集镇。
如果我说,他像一块黑色的石头,经过雕琢可以成为一块美玉,你当然不信。坐在风口上的人发质干燥,皮肤开裂,笑起来牙齿昏黄嘴唇扯出血丝,喉咙里嘶嘶得冒不出话,这些都不具备雕琢成为美玉的条件。他的旧房子在风口的转弯处,年迈的爷爷奶奶一有闲工夫就张嘴“捉捉捉”地唤鸡,这些都无法让他跳脱出来成为一块美玉。他生来就是他父亲那样的人,掉在闲杂的漩涡中不可分身,这样的人飞走了又会以别的方式回归,是命运般的被牵扯的风筝。
但我又觉得,他不是个喜欢吹大风的人。我在他的神色中捕捉到厌弃和不甘,挣扎和苦闷,他虽然站在风口假装很舒坦很平静,其实脚尖总是踮起来,是那种随时都可能跳开风口的站姿。于是我大着胆子跟他说,你可以将房子拢一拢,不要搞得整个山坡都像是你家的房子。你父亲是那样一个没有规划的人,他恨不得这个山都是他的,房子修得像蘑菇,这里一朵那里一朵。你应该修一座你喜欢的房子,稳稳地聚合起来,让它的气味和你相投。
这位少年并没有如我想象那样来一番动情的对话,而是反手从身后的裤包中抽出一罐杂牌酒,揭开就是一大口。我闻到一股浓烈的酒精味道。
“这才是和我相投的。”我猜他想这么回答,又不便开口。
之后他回到蘑菇屋抱出几个烧好的洋芋,这算是今天的晚饭。我们坐在风口处,和一条活蹦乱跳的瘦狗一起享用晚饭,风沙就在头顶盘旋,破胶纸就在头顶盘旋。
尔嘎说,如果干梁子有水就更好了,这儿晚上的月亮大得吓死人。
他像是带着一种期盼和愿望在说。喝了酒的人很难关闭心事。
干梁子肯定不会有水。掘地三尺也不会有。月亮再大也不会有。这儿的水从另外的山坡引来,浑突突还带着一股牲畜踩踏的气味。而选择这样的环境安家落户,你不得不说,那个喜欢吹大风的人一定在某一天突然疯了,才会抛弃他原先生活条件不错的老家。
然而我所想的未必就是尔嘎真正的心思。他也许很爱这个地方,之前我所看见的踮高的脚尖,搞不好只是一种飞翔的姿势,或者,他父亲张开双臂在这儿呼喊的时候就是这样的站姿。这是遗传性的,不能改变。
那么接下来我最好走开,让这颗石头在风口上尽量模仿他的父亲。他现在晕乎乎的,用方言重复着听不懂的酒话。我坐在这儿完全是多余的。我们的见面根本不必要。世界上的人,谁都没有必要天天窝在一起,谁十年不见谁,都应该感到庆幸——你终于可以不用活在别人的眼皮底下。
这太可怕了。我把自己丢进了死胡同。这场见面说到头是我要坚持的。至于尔嘎,他突然出现在眼前只不过是一种难以逃开别人眼皮的宿命。他是被我的好奇心牵到这儿来了,我仿佛听到什么人在高喊:
——如今蹲在风口处的他醉醺醺多么可悲。
——如今蹲在风口处的她眼睁睁看他的可悲。
——如今谁都帮不了谁却愿意窝在一起吹大风。
——那些风口上的灰尘和破胶纸啊,它们窝囊囊地飞走了。
我猛然从尔嘎旁边站起,我说,就当我是陌生人,你就在这儿过你的日子吧。不用改变你父亲遗传给你的吹大风的习惯。
他也猛然站起来——我不确定是他自己站起来还是风吹他起来——说,我早就看出来,你和其他人一样把我当成风口上不成器的石头,你们看到我父亲留下的那些别扭的房子——是啦,你说的这里一朵那里一朵的蘑菇——很不舒服,他把穷困潦倒像黄沙一样泼在这儿,搞得风口上的半空中全是破胶纸和灰尘,你可能还闻到了我父亲留下的房子中飘来的霉臭味。很不幸,你还得看着他儿子紧跟他的脚步喝酒、吹大风、口出狂言,你们都替我操心,三天两头打探我过得怎么样,有没有走上与我父亲不一样的道路,甚至分别十年,你们也会想方设法陪我蹲在大风口看看有什么大的变化。现在你看到了,我与十年前没什么两样。这儿缺水,只有干巴巴的大月亮,只有干巴巴卧在这儿看大月亮的石头!
我听了他的话很激动,一把将他推到风口的下方。
“大姑。”尔嘎站稳后吃惊地喊了我一声。我这才意识到先前走了心神,我仅仅是陷入一场幻想。
“我们刚才聊了很多。”我要掩饰点什么。
“啥?不记得了。”这是最好的回答,他喝多了嘛。
山下集镇上的灯火亮起来,尔嘎的那些散落的蘑菇屋也燃起微弱的烛火。由于他的房子分散,此刻蘑菇屋只有爷爷奶奶,他们无法将每一朵灯火都点亮。
夜色完全盖下来,谁都不想说话。但是我可以感觉身边少年的眼睛在望着山那边的路。那条路通向市区。通向市区之外的各个地方。
如果我说,今天晚上我们就出发,去流浪,去发疯。我敢保证他会跳起来举双手赞成然后又坐下去,他会给出这样的理由:我不是为自己活,我生来就背负了责任,我父亲的房子和他年迈的老父母,还在那些散落的蘑菇屋等着我回去。我的怂恿注定要毫无疑问地失败,这种事情放在哪儿都一样结果:天黑了淹没肉身,胆子会膨胀得跳出来,然而它无法见光,天不亮跑出去,天亮时哪儿来又回到哪儿去。如此反复,如此不自由。
“你该出去找点事情做,不要蹲在风口上,你的眼睛一定是风吹坏的。”我说。
“你信不信,我是个非常厉害的采玉的人——那种玛瑙石,听说过它是怎样挖掘的吗?明天晚上你来找我,我带你去长长见识。”尔嘎很得意。
为什么采玉要选在晚上呢,晚上看得清什么?但这个事情它对我有疯狂的吸引力。于是这天晚上的梦全都跟采玉有关。
第二天晚上我们出发了。尔嘎准备了电筒、水、饼干,还有一只破边碗,乱糟糟地搅在一只蛇皮口袋里。他戴了一顶旧毡帽,走在前边像个落魄的……打鱼的?……不,要饭的。这身装扮的好处就是,让一辆小四轮车的主人大发善心,将我们一直载到那个传说中藏了许多宝贝的山脚下。余下的山路差不多要走三个小时。
他作为领路人毫不客气地走在我的前面。这个时候我只好一步一步踩在他的脚迹窝。我感觉这个晚上他不是去采玉,而是专门为了领我走一截上坡路。这个地方潮湿险陡,走在前面的人就像踩在后面人的眼皮上。
“我想走前面。”我试探着说。
“这种路你走不惯,到处都是悬崖和树刺,必须要我这样熟路的人带领。”他又给我展现了得意的脸子。
我发现一点变化,这个少年坐在风口处和走在采玉的路上,完全不像同一个人。他坐在那儿是个年轻的有点心理负担的人,走在路上却爆发了流浪汉的潇洒。这条看上去黑黢黢的山路对我来说有几分可怕,说不定哪儿藏着一眼地洞,恰好等到我们的双脚踩下去,那可完蛋了。自从我离开山区到别的平坦的地方生活,近二十年没有走这么险陡的夜路,我原先走路脚趾内扣,能稳稳地抓住地面和随时绕开割人的石子,而现在我的脚趾可耻地失去这种功能,由于在别处长期走着平坦舒服的路,它们放松地抬着脑袋恨不得拱开我的鞋子——“去流浪,去发疯!”我差不多要听见这样的口号从它们那儿爆发。我伸手抹了一把汗,不知道这是汗水还是露水——这时候一股凉意蹿来,反正这儿的秋天冷起来很要命——两三颗星子洒在我们上空,昏沉沉的月光根本照不明地面,我感觉危险就藏在暗处,它可能正带着不必掩饰的夸张笑脸,等着我自投罗网。谁让我是一个走了和父亲不一样道路的人呢?现在我不得不将这种难走的路归罪于当初的选择。而父亲对这种夜路的熟悉就像对人生一样清醒,他绝对不会掉入陷阱也不会走一丁点弯路。
眼下我确实有点后悔,但不是无药可救的后悔。我心里还有一点“去流浪,去发疯”的狂欢。
…………
版权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