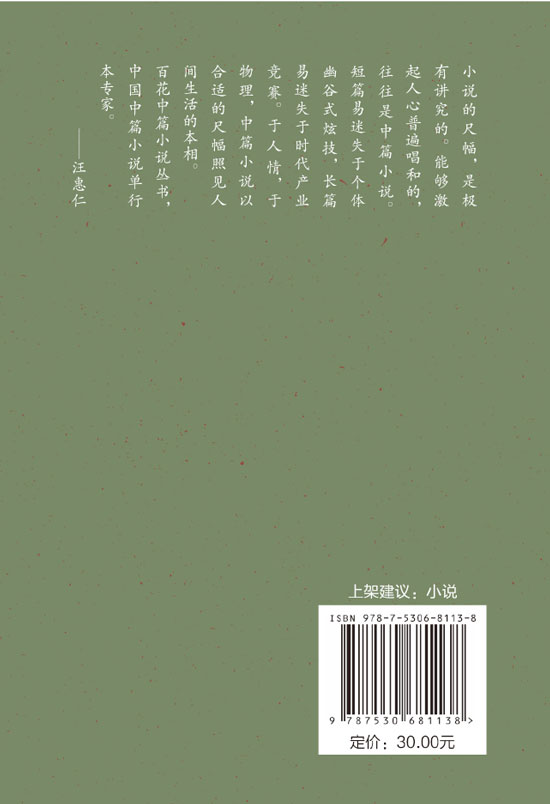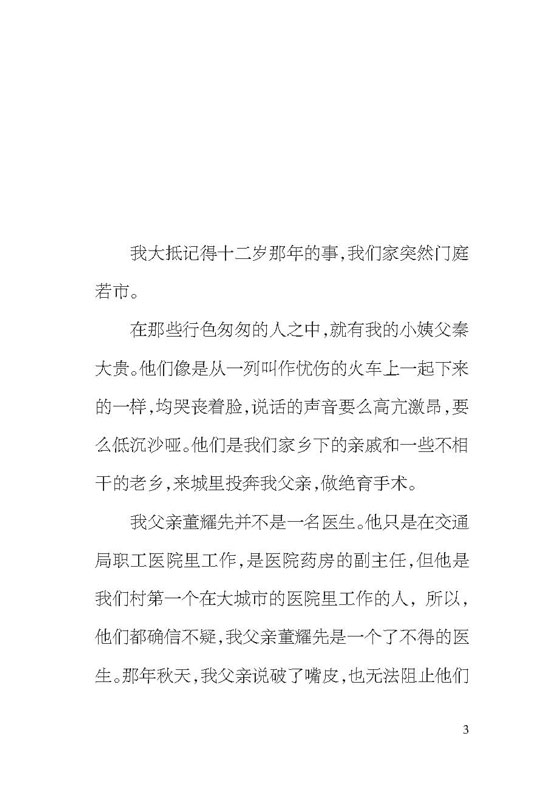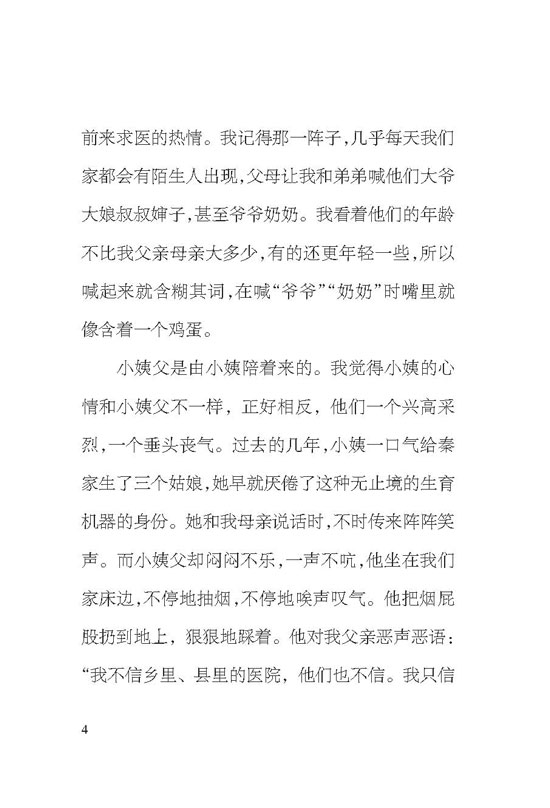图书简介
这篇《甘草之味》以改革开放为背景,书写了农民企业家秦大贵和通过自修成为医生的知识分子董耀先的命运沉浮,小说描写细腻、情节引人入胜,更展现出改革开放时代中不同领域人物的奋斗与成长。
作者简介
刘建东,1989 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 鲁迅文学院第十四期高研班学员。 1995 年起在《人民文学》《收获》《花城》等刊物发表小说。 著有长篇小说《全家福》《一座塔》、小说集《情感的刀锋》《黑眼睛》等十部。曾获人民文学奖、百花文学奖、孙犁文学奖、河北省文艺振兴奖等奖项。作品多次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小说排行榜。 现为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河北省作协副主席。
编辑推荐
刘建东是一位不断对小说题材以及表达形式进行多样性探索的作家。这篇《甘草之味》以改革开放为背景,书写了农民企业家秦大贵和通过自修成为医生的知识分子董耀先的命运沉浮,小说描写细腻、情节引人入胜,更展现出改革开放时代中不同领域人物的奋斗与成长。
小说卖点在于小开本,便于携带,有效填充大众读者的碎片化时间,机场候车、乘坐地铁等时间段,读者可以抛开手机进行深入阅读。当代作家的最新中篇不仅带有时代性、现实性,而且可以使读者站在小说阅读的最前沿,了解小说这种文学发展的新契机,对阅读时间、场地的要求进一步减少,鼓励大家去阅读,也符合国家全民阅读的号召。
这本书是百花社倾心打造的一款可以成系列的既长销又畅销的中篇小说单行本。依托《小说月报》的号召力,以最快的速度出版作者新近刊发的有寓意、有思想、有内涵的中篇小说单行本。
书摘
那些日子,父亲迷上了针灸,手痒痒得难受。他经常手里捏着一根银针在屋里踱来踱去,那银针的闪光晃得我弟弟董路生头晕,他说:“我头晕,到外面吹吹风。”他推开课本,一溜烟地跑了。父亲并没有停止读书和踱步。原来他在找合适的时机、合适的人选来练手。那天小姨父秦大贵是自投罗网。
吃完午饭,父亲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他把小姨父按到椅子上,卷起小姨父的裤腿,露出他瘦弱的膝盖和小腿。他拿出那个长条的小铝盒,打开,里面摆满了闪闪发光的银针。小姨父坐在那里瑟瑟发抖,他哀求道:“姐夫,我没病,不想扎针。”他眼里露出恐惧。
父亲轻描淡写地说:“你怕啥,谁没扎过针?一点也不疼。就跟被蚂蚁咬了一口一样。你连蚂蚁都怕,亏你还当过兵。”
“我没病,扎啥针。”小姨父反复强调这一点。
既然父亲找到了最合适的对象,他岂能善罢甘休!他按住小姨父因为恐惧而晃动不已的肩膀,就像当年结扎前安慰他一样:“没事的。一点也不疼。有没有病你知道啊?很多人得了病自己并不知道,你也是。我早就在观察你走路的姿势了,你一条腿总是向外撇,这说明你腿上的气血不畅,腿上的气血不畅就说明你有潜在的疾病,轻则腿脚麻木,重则半身不遂。”
不容分说,父亲把银针用酒精消过毒,便毫不留情地在小姨父的膝盖处下了手。小姨父及时地从兜里掏出一片甘草,快速地送进嘴里,响亮地吸了一口。我和弟弟都好奇地围着他们,睁大眼睛看着小姨父抖动的膝盖和脚踝。我母亲劝父亲:“他不愿意,你就别扎了。”
父亲固执地抢白母亲:“又死不了人,我这是在给他治病。他还得感激我呢。你说是不是?”他转身对小姨父说。
小姨父早就忘了该怎么说话,他的脸色发青,嘴唇发紫。
母亲不忍看,转身出去了。
小姨父的反应异常强烈,父亲的银针还没扎到他腿上,他就扭动身体,大呼小叫。父亲警告他:“你要是乱动,扎错了穴位,就不是我的事儿了。”
这句话真管用,小姨父立即吓得僵在椅子上,脸色由青变白,他颤抖着说:“姐夫啊,看在咱们是亲戚的份儿上,你一定要扎准了啊。”
父亲镇定自若地说:“放一百个心吧。我在梦里不知道扎了几百遍了。一点问题没有。”
不管父亲再怎么吹牛,毕竟这是他头一次针灸,再加上小姨父紧张得仍然有些晃荡的身体,父亲的自信心便打了些折扣。他的手也随着小姨父的身体晃来晃去,但内心那股无法遏制的兴奋,让他还是果断地扎下了第一针。于是我们便听到了小姨父那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看到了他腿上的鲜血。父亲也慌张了,他一时不知道下一步要干什么,而扎上去的银针还随小姨父的身体不停地摇动着。母亲应声从外面跑过来,惊呼道:“咋了咋了,让你不要扎不要扎,你偏不信邪,自己又不是个医生,装啥大头蒜。”
父亲的第一次尝试以失败告终。可他并不气馁,那几天他吃不下睡不香,都在琢磨着为什么会失了手,他自言自语:“按理说不应该呀。没错呀,一切都是按程序来的呀。不会错的呀。”他还去请教医院的老中医邢大夫,那个戴着厚厚镜片的老医生。
父亲还去澡堂的锅炉房找过小姨父,问他到底那天扎得疼不疼。小姨父煞有介事地摸摸膝盖,说:“疼吧。”
父亲追问:“你好好想想,到底疼还是不疼?”
小姨父犹豫了:“好像有点疼。”
“到底疼不疼?”父亲并不死心。
“好像又不怎么疼。”小姨父说。
这些后来父亲在饭桌上转述给我们的话,让他彻底放下了心理包袱,他开始了又一次的冲刺,他摩拳擦掌,信誓旦旦。那个礼拜天他特意去请小姨父来家里吃饭。这让小姨父受宠若惊,连买一包黄金叶烟的惯例都忘了。父亲举着银针,问他:“真的不疼是吧?”
小姨父说:“不疼。”
其实,第二次还算是成功的。没有见到血,也没有听到小姨父的叫声,只是小姨父额头上的汗水比往常要多许多。所以,那个春天里,一到礼拜天,小姨父就成了我父亲练习针灸的靶子,他身体的各个部位都是我父亲下针的地方。身上扎满银针的小姨父,很安静地坐在椅子上,或者躺在床上,早就没有了恐惧与担忧,他甚至还自得地看着《人民日报》。他鼓励父亲说:“姐夫,一扎针我就觉得浑身舒坦,跟洗了次澡一样。”
父亲见怪不怪地说:“洗澡哪能跟扎针比。洗澡只是把你身上的脏东西洗掉,扎针却是把你身体里的脏东西扎没了。”
有时候小姨父浓密的黑发丛中也长出来几根银针,而他低着头在那里看《人民日报》,很享受的样子。我问:“小姨父,你说的大事,啥时候来呀?”
他指点着报纸说:“快了快了。你就等着吧。有比你还急的人。”
我一直好奇小姨父为什么坚持说第一次扎在他身上的针不疼。他从来没有说过。这是他和父亲的一个秘密。
我不知道小姨父说的大事是什么,可是发生在他和我父亲身上的大事却来了。
版权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