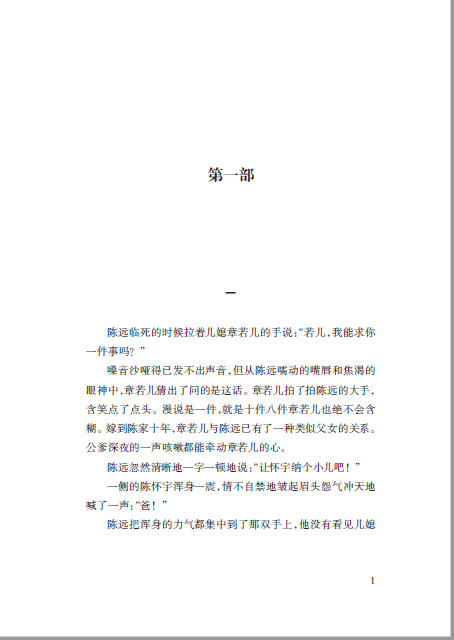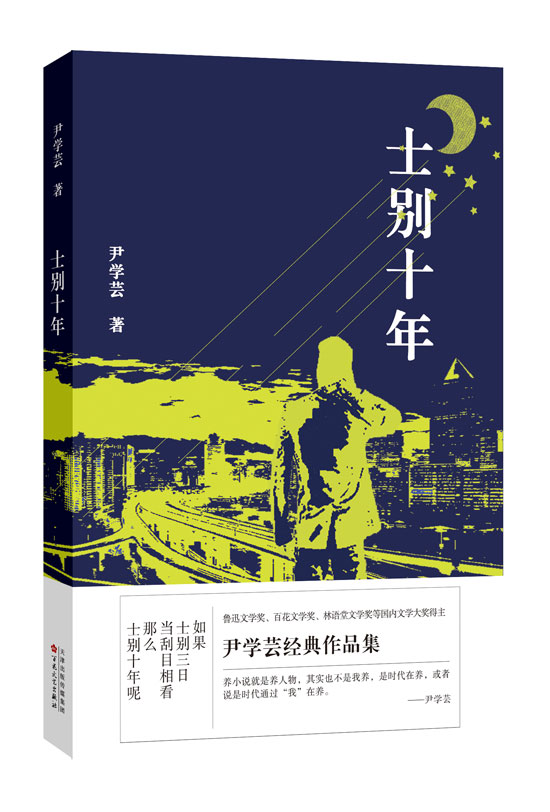图书简介
血与火洗礼过的冀东大地,近百年波澜壮阔的社会人生图景,性格迥异的姐妹在历史的长河中拼搏抗争,造就了不同的人生际遇。李勋一生都在寻找和等待爱情。李荃则始终不忘参加革命的初心,追求光明。两姐妹都有自己的执念,一个是为爱情,一个是为光明。小说以女性命运观照时代、社会,用历史、文化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女性的命运。
作者简介
尹学芸,女,1964年生。80年代末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已发表各类文学作品三百多万字。曾在《青年文学》《上海文学》《北京文学》《天涯》《清明》《时代文学》等三十多家报刊杂志发表文学作品。作品多次被各种选刊选载。曾获首届梁斌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孙犁散文奖、林语堂文学奖、百花文学奖和《北京文学》优秀作品奖等奖项。并多次登上《收获》文学排行榜、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等多个权威文学榜单。现为天津市作家协会文学院签约作家。著有《难得浪漫》《女人是祸水》《我爷爷与大刀梁英》《家园》《盛夏》《怀念三毛》《士别十年》《李海叔叔》《望湖楼》《菜根谣》等作品。短篇小说《难得浪漫》获天津市首届文学新人奖。中篇小说《女人是祸水》和《我爷爷与大刀梁英》获天津市文化杯小说大赛一等奖。小说《家园》获人民文学颁发的全国文学作品大赛创作奖。短篇小说《盛夏》、诗歌《怀念三毛》获天津市文化杯文学大赛二等奖。散文《心底流出来的不都是歌》入选香港皇冠出版社出版的《当代百名作家散文选》。2017年12月《士别十年》获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中篇小说奖。2018年8月11日《李海叔叔》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2019年1月5日《望湖楼》入选“《扬子江评论》2018年度文学排行榜”中篇小说类第8名。
编辑推荐
《岁月风尘》呈现了近百年波澜壮阔的社会人生图景,通过描述李家、陈家的家族史,塑造了两个性格各异的女性人物形象,极大丰富了新时代文学的人物形象画廊。
小说主人公李荃和李勋是一对亲姐妹,历尽千般磨难,终生都没有向命运妥协,在历史的长河里,两人不同的性格造就了不同的人生际遇。李勋一生都在寻找和等待爱情。李荃则始终不忘参加革命的初心,追求光明。两姐妹都有自己的执着,一个是为爱情,一个是为光明。作品以女性命运观照时代、社会,用历史、文化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女性的命运。
生命在百转千回中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成长。我们奈何不得岁月,任由它像河流一样向前奔涌。时过境迁,唯有一样能留住,那就是我们对亲人和家国深沉的爱。
书摘
第一部
一
陈远临死的时候拉着儿媳章若儿的手说:“若儿,我能求你一件事吗?”
嗓音沙哑得已发不出声音,但从陈远嚅动的嘴唇和焦渴的眼神中,章若儿猜出了问的是这话。章若儿拍了拍陈远的大手,含笑点了点头。漫说是一件,就是十件八件章若儿也绝不会含糊。嫁到陈家十年,章若儿与陈远已有了一种类似父女的关系。公爹深夜的一声咳嗽都能牵动章若儿的心。
陈远忽然清晰地一字一顿地说:“让怀宇纳个小儿吧!”
一侧的陈怀宇浑身一震,情不自禁地皱起眉头怨气冲天地喊了一声:“爸!”
陈远把浑身的力气都集中到了那双手上,他没有看见儿媳章若儿的一双小手在自己的那双大手里已经由白变红。一双眼球似乎要脱离眼眶,里面布满了死亡的阴影。他根本无暇顾及儿子说了什么,儿子说了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儿媳,是这个叫章若儿的女人,是这个像亲生闺女但终究不是亲生闺女的人。这种场面陈远已经演习了若干年,自从他知道章若儿生不出一男半女,知道儿子儿媳婚前有约,摒弃一切陈规陋习,陈远就始终期待着这一天。这一天太过久远和漫长,陈远等得心力交瘁。他知道章若儿不会跟一个快要死的人一般见识,除此之外,他别无办法。这当然是章若儿极不情愿的,陈远想,新派也不是这么个新法,新派也不能让人绝后。陈远蓄谋已久的日子终于到了,当举着招魂幡的小鬼迈进门槛时,陈远终于说出了那句话。陈远的两只大眼一眨不眨地盯着章若儿,这最后的时间他拿捏得恰到好处。章若儿潸然流下了两行长泪。她没有理会丈夫陈怀宇,而是朝公爹深深地点了点头。一丝微笑像条蚯蚓爬上了陈远的嘴角,然后僵死在了那张脸上,陈远闭眼的动作十分缓慢,仿佛两扇打开了太久的门,关上它们是一件力不从心的事。
四月的雨水打湿了墙上挂着的那把胡琴,因为久不动它,胡琴在陈怀宇的手里显得古里古怪。胡琴曾经是父亲的心爱之物,每天晨起或黄昏,都有一段行云流水般的曲调响彻陈家大院。父亲是一个讲究意境的人,他让村里最好的木匠设计了一个别致的琴凳,凳面呈凸形,三只脚都壮实得有些过分,通体雕刻着花鸟鱼虫。父亲从不在卧室和客厅拉琴,父亲喜欢在庭院的凤尾竹下或石榴树旁。父亲的琴拉得好听,可惜陈怀宇不懂。陈怀宇尽了最大的努力也没弄明白父亲手下流出来的乐曲是怎么回事。事实证明父亲让陈怀宇不懂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父亲从不流露对儿媳章若儿的不满,从不把没有孙男娣女的事当回事。为此章若儿心底存下的那份感激比山还厚。
难道这一切都是假象?
陈怀宇望着蒙满灰尘的胡琴呆呆地想。父亲把自己的心事掩藏了十年而且掩藏得滴水不漏?父亲活着是不愿意让章若儿为难还是不愿意让自己为难?父亲估算到了自己的百年之日会来得这样早?陈怀宇调整了一下琴弦,想像父亲一样随便拉出来个曲目,胡琴发出了硬邦邦的“吱嘎”声,把陈怀宇吓了一跳,陈怀宇没有想到胡琴还能发出这么难听的声音。陈怀宇有些惊恐地想,父亲没了什么都不一样了,父亲走了却把魂魄留下了,父亲真不枉做父亲啊。
结婚十年,陈怀宇只能用两个字形容自己的婚姻生活:幸福。他和章若儿是自由恋爱结的婚,在偏远的乡村,自由恋爱而成婚姻几近神话。那时,他正在通州的一所师范学校求学,一次集会时,认识了低他一年级的章若儿。陈怀宇几乎在认识章若儿的同时就爱上了她。章若儿美丽的脸庞总有一种忧戚,一双杏眼饱含汁水,似乎随时都能洒下杏花雨。陈怀宇经常呆呆地想,世上还有如此让人挂心的女子,不知有怎样的遭际命运。女生寝室外面有株大柳树,陈怀宇手持一卷诗书在树下吟诵的场景看傻了许多人,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女学生们不知道他是谁,为了谁,直到有一天,章若儿从寝室跑出来站到了柳树下,同学们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章若儿是通州府大户人家姨太太的女儿,母亲早丧。舅舅供她上学,可这学她上得提心吊胆,总怕有一天会出意外。一天临近傍晚,一挂马车来拉她的行李铺盖,车夫见面给她道喜,说家里把她许给了京城一个玩罐王八的阔少,三天之后就是喜期。章若儿急急来找陈怀宇商量对策,校园内外却遍找不到。车夫抱着铺盖放到车厢里,一声一声催得紧。章若儿就要上车了,却见身着蓝布长衫的陈怀宇匆匆朝这边走来。他是从校园外面的五道庙子赶来的,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在那里商谈革命与政治,共同发下誓愿:弃笔从戎,奔赴杀场,解民众于倒悬。他们孩子气地以水当酒,并把庙里的陈年老灰撒到碗里,作为天地凭证。别人都喝了,陈怀宇在关键时刻却犹豫了。“等一等,容我问问章小姐。”他放下水碗匆匆赶回了学校,却见章若儿一跃从车上跳下。章若儿对陈怀宇说:“两条路。跟你走,或者我这一走此生永不再见。”陈怀宇一下急出了眼泪:“就不能宽限些时日吗?”章若儿扭过头去,背后就是那辆马车,驾辕的白马不安地踏着马蹄。车夫蹲在轱辘旁抽烟,眼里是看杂耍一样的轻慢。章若儿说:“你问他宽不宽限。”车夫懒洋洋地站起身,从车帮的叉套里抽下马鞭,放下了车闸。陈怀宇什么也没说,用手一牵,章若儿跟他走了。
西边的那片晚霞悄然消失了,只有轻烟般缥缈的一只雁影,是一只孤雁。陈怀宇注意它已经很久了,它寻寻觅觅地在空中盘旋,偶尔发出一声悲鸣。陈怀宇的心空了,革命与政治激发起的热情被清凉的晚风抽走了。他拥紧了怀里的章若儿,感受到了她像风中的柳叶一样单薄。他想,这就是命运了。命运在他需要选择的时候送来了章若儿。革命需要他,可爱情不更需要他?也许还是父亲说得对,宏图大志和远大理想有时更像过眼烟云。父亲希望他去从事乡村教育,让那些吃不起饭的孩子也能认识几个字。陈怀宇一直认为这是将来的事,可将来又在哪里呢?陈怀宇忽然有些感伤,几个小时前的那个激动人心的场面一下子变得遥不可及。他与盟兄李景阳和另外几个同窗好友共同发下的誓愿,言犹在耳,没想到事情变得这样快,章若儿一句话,就改变了他的航程。陈怀宇百感交集,在痛苦和悲壮中吻了章若儿。陈怀宇的“背叛”行为遭到了同窗好友的一致声讨,只有盟兄李景阳一声不吭。当大家再也无话可讲时,李景阳站起身来说:“怀宇,照顾好章小姐,你就是为国出力了。革命的事就交给我们吧。”
陈怀宇一躬到底,抬起头来已经是满面泪水。
章若儿没有拿到毕业证书,那个玩罐王八的京少总来骚扰。她索性提前退学,同陈怀宇来到了他的家乡柳树堡。章若儿的到来使陈家大院喜庆了好长时间。对这个自己送上门来而且不带一份陪嫁的媳妇,陈家人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尊重。章若儿说话温和,举止得体,对谁都是一张笑脸,她是打心眼里爱这方水土。两三年的时间,章若儿就成了整个家庭的中心,不论大事小事,人们都习惯向她讨个主意,章若儿总能把事情办得圆满,让上上下下都无话可说。陈怀宇的学堂开课那天,只有家境好的子弟三五人,章若儿一家一家地说,一个一个地请,最后连放牛的孩子都来了。村里的那份喜庆和热闹,自从盘古开天地都没有过。
只是章若儿不能生养,柳树堡都为之叹息。
十年就这样过去了。章若儿从一个单薄的女孩变成了丰腴的少妇。十九岁到二十九岁的韶华在这里打个结,公爹陈远撒手尘寰。原来他有心事,只是到临死才肯说出口。“我能求你一件事吗?让怀宇纳个小儿吧!”他的眉头皱成了蒜疙瘩,吐出的每一个字都透着不耐烦。
天渐渐黑了,绵绵雨水仍是无尽无休的样子。青灰色的瓦垄成了一道一道的小溪,在窗前结成了一片水帘。陈怀宇把胡琴重又挂好,遥遥打量着卧房。这里与卧房成夹角,一片烛光的影子在窗上腾挪。陈怀宇好生纳闷,这可是一件久违了的事。在陈怀宇的印象中,只有新婚的洞房如此明亮如此灿烂过。陈怀宇记得很清楚,当时洞房里家人只点了六根红蜡,取“六六大顺”之意。凡事都不挑剔的章若儿却执意要再点上六根。于是洞房里像升起了一个小太阳,烛光把屋子的四壁都照得雪亮。“我喜欢。”章若儿低声呢喃,“我做梦都想着有这么一天,被一片烛光包围,和自己的男人一起告别以往的岁月。过去这个男人没有名字。我不知道他姓甚名谁,长相如何,直到你出现在那株柳树下,我才坚定了信念。从此我的枕边总要空出你的位置。冬天我为臆想中的你盖好被子,夏天我手里的扇子摇啊摇啊,只为心里有一个熟睡的你……”
陈怀宇听见自己的喉结咕噜响了一声。
一股巨大的力量像轰然作响的瀑布一样席卷了他。其实他看见了门楣上悬挂着的油布雨伞,但张伞是一件多麻烦的事啊!陈怀宇冲进了雨中,清凉的雨滴落在他滚烫的皮肤上,烫得吱吱有声。他裹挟着一股凉气闯进卧房,却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
身着一身缟素的章若儿盘坐在炕上,端庄的一张脸上隐忍着忧戚。泪痕十分明显,虽然微笑已经像浮雕似的显露了。“若儿。”陈怀宇仓促地叫了声,一下僵住了。
“父亲说得很对。”章若儿抬头看着他,轻轻说,“父亲去世了两个月,我想了两个月。今天坐在这片烛光里,我都想明白了。过去我们认真地玩了儿戏,因为那时我们是两个大孩子。现在不同了,父亲故去,我们自己就成了大人。我们理应按照父亲的吩咐去做,你说呢?”
陈怀宇一时没有回过神来,他茫然地问:“我说?我说什么?”
章若儿拉他在自己的身边坐下,说:“这么快就把父亲的遗嘱忘了?”
“我想都懒得去想。”陈怀宇颓然说,“我只是有些奇怪,他哪里来的怪念头。”
“一定要认真想。”章若儿说,“这不是一件小事。”
“怎么,你当真了?”陈怀宇说得有气无力。
“当不得真吗?”章若儿幽幽看着他,“父亲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留下的遗愿,当不得真吗?”
“当不得。”陈怀宇站起身,果断地说,“这件事在我的心中连一片影子都没有留下。父亲如果为自己的事留下遗嘱,再难办的事也要办,可父亲是一个多开明多重道义的人啊,他从不干涉我们的事。你进陈家的门已有十年,难道还没有体会吗?我们完全可以当父亲什么也没说。或父亲神智昏迷时说的这话。父亲在天国里也会为给你出了难题而不安的。何况父亲那么了解我们。我们恩爱异常,我们摒弃一切旧的、传统的、世俗的东西,与这个社会制度势若水火,我们没有能力改变什么,但我们独善其身,绝不同流合污。这些难道你都不记得了吗?”
章若儿注视着眼前腾跃的烛火,什么也没说。这情景酷似十年前的那个夜晚,但十年毕竟是一段不短的岁月。章若儿发现自己在这十年里有了明显的变化。十年前烛光里的章若儿还只像一颗葡萄,酸甜只是一兜水儿,而十年后章若儿发现自己更像一只熟透了的石榴,薄薄的皮里面长的是饱满结实的籽。
章若儿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
版权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