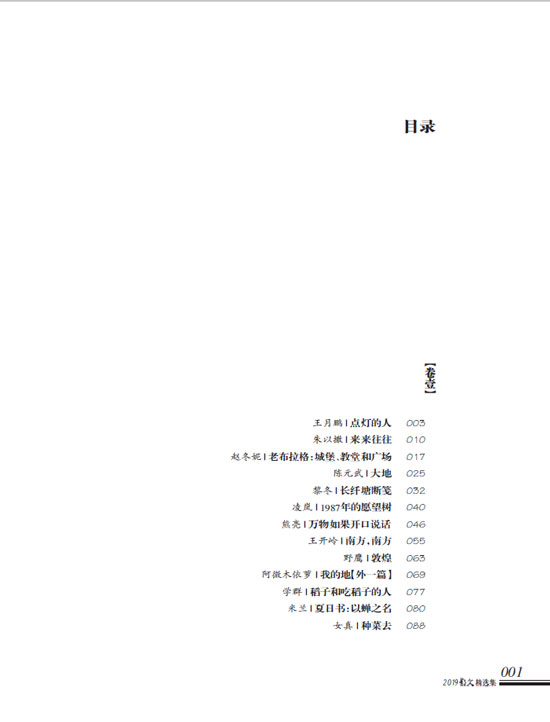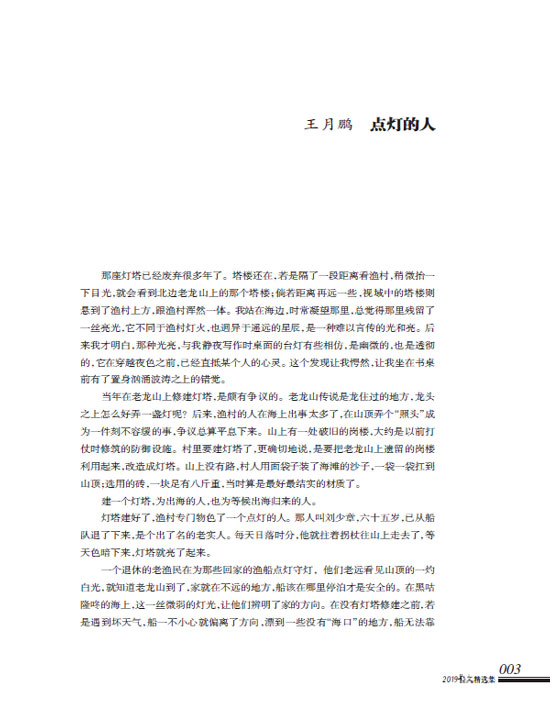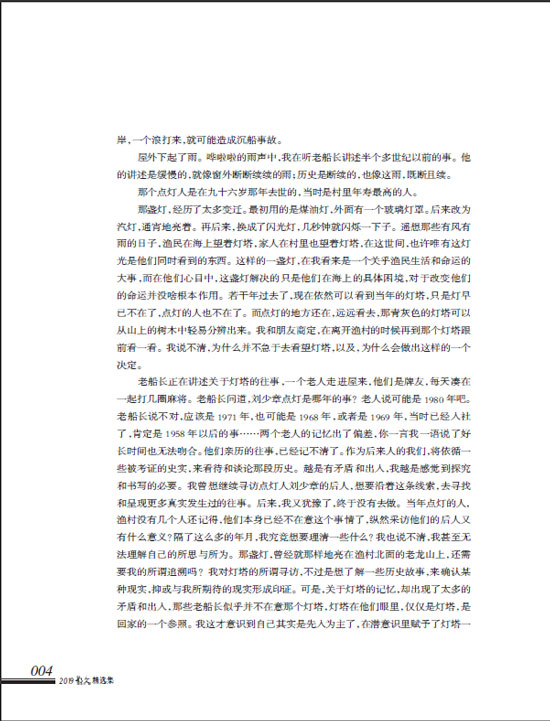图书简介
收入《黑夜里的麦田》《忽略》《以鸟鸣春》《敦煌》《万物如果开口说话》等五十余篇文章,有反映历史人文主题宏大的篇章,有记叙风花雪月意趣闲适的雅致小品,更多的是切入生活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集《散文》2019年度刊发的实力作家与文坛新秀的力作佳作之大成。
作者简介
由《散文》编辑部统筹编选,作者阵容既有朱以撒、李汉荣、李万华、刘荒田、学群、玄武这样的笔力雄厚的实力作家,也有初露锋芒的新锐作家如走昭、李琬等。
编辑推荐
秉承《散文》杂志所一贯坚持的散文创作立其诚、传其美、出其新的高格调要求,多角度地展现当代散文文坛创作面貌,既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亦不乏高度的文学性和思想性,是值得期待的一部散文作品集。
书摘
点灯的人
王月鹏
那座灯塔已经废弃很多年了。塔楼还在,若是隔了一段距离看渔村,稍微抬一下目光,就会看到北边老龙山上的那个塔楼;倘若距离再远一些,视域中的塔楼则悬到了渔村上方,跟渔村浑然一体。我站在海边,时常凝望那里,总觉得那里残留了一丝亮光,它不同于渔村灯火,也迥异于遥远的星辰,是一种难以言传的光和亮。后来我才明白,那种光亮,与我静夜写作时桌面的台灯有些相仿,是幽微的,也是透彻的,它在穿越夜色之前,已经直抵某个人的心灵。这个发现让我愕然,让我坐在书桌前有了置身汹涌波涛之上的错觉。
当年在老龙山上修建灯塔,是颇有争议的。老龙山传说是龙住过的地方,龙头之上怎么好弄一盏灯呢?后来,渔村的人在海上出事太多了,在山顶弄个“照头”成为一件刻不容缓的事,争议总算平息下来。山上有一处破旧的岗楼,大约是以前打仗时修筑的防御设施。村里要建灯塔了,更确切地说,是要把老龙山上遗留的岗楼利用起来,改造成灯塔。山上没有路,村人用面袋子装了海滩的沙子,一袋一袋扛到山顶;选用的砖,一块足有八斤重,当时算是最好最结实的材质了。
建一个灯塔,为出海的人,也为等候出海归来的人。
灯塔建好了,渔村专门物色了一个点灯的人。那人叫刘少章,六十五岁,已从船队退了下来,是个出了名的老实人。每天日落时分,他就拄着拐杖往山上走去了,等天色暗下来,灯塔就亮了起来。
一个退休的老渔民在为那些回家的渔船点灯守灯,他们老远看见山顶的一灼白光,就知道老龙山到了,家就在不远的地方,船该在哪里停泊才是安全的。在黑咕隆咚的海上,这一丝微弱的灯光,让他们辨明了家的方向。在没有灯塔修建之前,若是遇到坏天气,船一不小心就偏离了方向,漂到一些没有“海口”的地方,船无法靠岸,一个浪打来,就可能造成沉船事故。
屋外下起了雨。哗啦啦的雨声中,我在听老船长讲述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他的讲述是缓慢的,就像窗外断断续续的雨;历史是断续的,也像这雨,既断且续。
那个点灯人是在九十六岁那年去世的,当时是村里年寿最高的人。
那盏灯,经历了太多变迁。最初用的是煤油灯,外面有一个玻璃灯罩。后来改为汽灯,通宵地亮着。再后来,换成了闪光灯,几秒钟就闪烁一下子。遥想那些有风有雨的日子,渔民在海上望着灯塔,家人在村里也望着灯塔,在这世间,也许唯有这灯光是他们同时看到的东西。这样的一盏灯,在我看来是一个关乎渔民生活和命运的大事,而在他们心目中,这盏灯解决的只是他们在海上的具体困境,对于改变他们的命运并没啥根本作用。若干年过去了,现在依然可以看到当年的灯塔,只是灯早已不在了,点灯的人也不在了。而点灯的地方还在,远远看去,那青灰色的灯塔可以从山上的树木中轻易分辨出来。我和朋友商定,在离开渔村的时候再到那个灯塔跟前看一看。我说不清,为什么并不急于去看望灯塔,以及,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
老船长正在讲述关于灯塔的往事,一个老人走进屋来,他们是牌友,每天凑在一起打几圈麻将。老船长问道,刘少章点灯是哪年的事?老人说可能是1980年吧。老船长说不对,应该是1971年,也可能是1968年,或者是1969年,当时已经入社了,肯定是1958年以后的事……两个老人的记忆出了偏差,你一言我一语说了好长时间也无法吻合。他们亲历的往事,已经记不清了。作为后来人的我们,将依循一些被考证的史实,来看待和谈论那段历史。越是有矛盾和出入,我越是感觉到探究和书写的必要。我曾想继续寻访点灯人刘少章的后人,想要沿着这条线索,去寻找和呈现更多真实发生过的往事。后来,我又犹豫了,终于没有去做。当年点灯的人,渔村没有几个人还记得,他们本身已经不在意这个事情了,纵然采访他们的后人又有什么意义?隔了这么多的年月,我究竟想要理清一些什么?我也说不清,我甚至无法理解自己的所思与所为。那盏灯,曾经就那样地亮在渔村北面的老龙山上,还需要我的所谓追溯吗?我对灯塔的所谓寻访,不过是想了解一些历史故事,来确认某种现实,抑或与我所期待的现实形成印证。可是,关于灯塔的记忆,却出现了太多的矛盾和出入,那些老船长似乎并不在意那个灯塔,灯塔在他们眼里,仅仅是灯塔,是回家的一个参照。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其实是先入为主了,在潜意识里赋予了灯塔一些象征的意味。这是所谓知识分子通常的思维习惯,这样的思维习惯在渔民身上是无效的。在当年的渔村,灯塔仅仅是灯塔,这不是象征,也不是细节,这是关涉海上航行的生命,关涉到渔民能否安全回家的一件很具体很紧要的事。我需要做的,是努力从象征的思维中跳出来,回到真切的现实,回到事件的现场。
村人对灯塔的记忆大多淡漠了。几个与灯塔有些关联的老船长,也只是记住了大概情节。时光带走了太多东西。我对灯塔往事的追问,在他们也是有些不解的。我试图用我的方式来看待这个渔村,与这个渔村的现在和历史对话。但是事实证明,我与渔村的对话,是不对称的,也是无效的。关于灯塔,在渔村有不同的说法,每个说法都来自亲身的经历。是否需要统一这些说法,这是一个问题。我曾想,把这些问题以分歧的状态留下,留待后人鉴别和评判。太多的历史史实不都是这样交付给了更为漫长的时光?可是,脱离了特定语境,所谓的鉴别,所谓的评判,所谓的看到和理解,又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当时的真实状况?
老船长说,他1992年退休的时候,灯塔还在用着。在他身后的墙上,是一张山东省地图和世界地图,那是他时常要看的。如今,在地图之上,在巨大的“寿”字两边,挂起了一副对联,那是他八十大寿的时候,亲戚送他的贺礼——“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大红的对联盖住了墙上的那张旧地图。老船长坐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讲述关于灯塔的故事。
他一直记着五岁那年的一个秋天傍晚,跟随爷爷去山上点灯的情景。天下着雨,他们披着蓑衣,沿着曲曲弯弯的小路向山顶走去。夜色越来越浓,爷爷手中的那盏灯在风雨里或明或暗,发出不服输的光。他跟在爷爷的身后,提着一桶油,那是汽灯备用的油。沿着山路缓慢地挪动了大约有一个小时,才到达山顶。爷爷点上汽灯,遥望海面,长长地叹一口气。下雨天看不清海上,只看到黑乎乎的一片。船头即使悬挂了小汽灯,在山顶也是看不到的。爷孙俩需要在山上住一晚上。小屋里漏雨,根本就无法入睡,他看着那盏汽灯一直亮着,那个时候他幼小的心灵中并不知道,这盏灯对于海上航行的村人意味着什么。若干年后他当了渔民,当了船长,时常会想起五岁那年跟随爷爷在山顶守灯的雨夜,他似乎更深地理解了那盏灯的意义。再后来,大约是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山顶拉上了电灯,不再需要有人每天上山点灯了,在渔村的房屋里,就可通过电闸遥控山顶的那盏灯。那盏灯,也像其他地方的灯一样,在山顶闪烁,老渔民根据灯的闪烁频率,判断自己到了哪里。灯光作为一种语言,穿越夜色和风雨,被理解和被接受。在海上,两船相遇,也是通过灯来传递信号的,“左红右绿当中白”。他补充说,这是那个年代的国际航海规定。
五岁那年陪爷爷上山点灯的他,如今已经六十多岁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就这样走过。不管走在哪里,他的心中始终有一盏灯在亮着。我知道,当我写下这个句子,它瞬间被赋予了象征意义,然而对于眼前的这个老船长,这一盏灯,是现实中的灯,微弱的光里,有着切肤的迷茫与希望。
“老辈人出海,太苦了,村里很多人都是死在海里的。过去只要遇到了风,技术好的渔民能回来,有的船就顺风漂到了别的地方,最终船翻人亡。”村里新建的房屋,门楣大多贴有“一帆风顺”四个字。这个词语,在我们的惯常使用中,是有隐喻意味的,而在这个渔村,这是最具体的祈愿,不是形而上的,是现实中的正在经历和即将经历的事。后来,每条船上都买了“半导体”,渔民感到很好奇,他们不明白一个小小的机器怎么会说话,而且可以预知天气的好坏。他们把它称为“话匣子”。他们在海上拿着那个小小的机器,反复地端量,觉得这真是一件神奇的事。他们经年累月在海上打鱼,经历了太多的事,再神奇的事都可以在他们或清晰或模糊、或犹疑或坚定的“理论”里得到解释,而现在这个小小的“话匣子”却让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了。这是他们对于科技最初的态度和记忆……时光转眼到了今天,船上完全是机械化了,先进的仪器,导航、探鱼器,他们都习以为常。是科技,减少了海上的危险,祖祖辈辈出海打鱼的渔民,靠运气和经验在海上作业的渔民,如今可以凭借高科技做出精准判断,实施精准捕捞,海里的资源越来越少。
他说起小时候提着篓子到海边就可以捡到被海浪打上了岸的鱼,有一种当地人称作“离水烂”的鱼,很快就会捡满篓子,他和他的小伙伴们把这种鱼捡回家,用来喂猪。而如今,所有的鱼都明显“瘦”了。有的渔民在网里再套上一层纱网,让网口变得越发小了,再小的鱼也休想“漏网”,甚至连产卵期的鲅鱼,都被他们捕走了。在休渔期,有人仍在偷偷出海,连鱼苗都捞了上来。我们习惯了说“海阔凭鱼跃”,其实在浩瀚的大海里,鱼类也是讲究“水土”的,哪种鱼在哪种地方产卵生长,都是有规可循的。比如,有一种大青虾,每年都会到渤海湾里产卵,它们钻在海底的沙里,一边产卵一边吃沙,虾籽沾在沙上。春天的鱼,大多是带籽的。这种时节,人是不该打搅它们的,更不该捕获和食用它们。前几年,有外地人把定置工具插在渔村附近海域,那是一种“断子绝孙”式的捕鱼方式,再小的鱼苗也不放过。村里的渔民试图制止他们,却遭到了殴打。周边几个村的渔民自发组织起来,驾着自家的船,足有上百艘,浩浩荡荡地拥向外地人占据的海域讨要说法,直到有关部门出面,这事才算平息下来。
眼前的这位海木匠已经九十四岁了。他回忆小时候,渔村家家都有小船,家家都有捕虾的网,他的父亲当时在海会工作,每年开始捕虾之前组织渔民抓阄,所有渔船按照抓阄的位置在海上有序排列,互不侵扰。渔船出海归来,橹都统一放在龙王庙以东的小棚里,由专人看护。海木匠目前所住的这栋房子,是四十四年前盖的,房子东面市场处当时是海,从平房上即可甩竿钓鱼,外面有坝,坝高不足一米,平时海潮一般不会超越,风大的时候,海浪翻过堤坝,撞到墙上,浪花径直溅进了院里。每天晚上,他都是枕着海的声音入睡的。他说,以前渔灯节送灯是在晚饭后,现在改成了白天;以前每到正月十三这天渔村海面灯火闪烁,真好看,现在放灯常常就被船和海上养殖挡住,根本就放不出去。
这个渔村的“农转非”是在2008年12月28日,海木匠记得特别清楚,他说他的新生活是从那一天开始的。他曾在长春打工做过木匠,回村后出了几年海,1962年秋天到了渔村船厂工作,成为一名海木匠,主要任务就是造渔船。造渔船又称排渔船,由专门的海木匠施工。开工之日,先铺船底三块板,名为“铺志”,要放鞭炮,念喜歌,宴请工匠;渔船造到船面,举行仪式,称“比量口”,用红布包裹铜钱放入渔船底盘中间;最后的仪式是“上梁面”,安梁时,在船上做一个小洞,内放铜钱,用红布覆盖,再用面梁压住。村里在老龙山上修建灯塔,灯座是由这位海木匠亲手安装的,他和村里的瓦匠一起忙活了一个星期……老人思维清晰,记忆力很好。我想要继续打听关于灯塔的往事,老人却话锋一转,谈到了他的童年。他说小时候的腊月里经常下大雪,雪花飘啊飘,现在再也看不到那么大的雪了,有时候一个冬天也见不到雪花,反而是南方经常下起了大雪。他感慨这个世道的变化。我对这个世界一直是怀有困惑的,且经常把这种困惑归结为不成熟所致。面对这位九十四岁的老人,听他慨叹对世事的困惑,我感到释然。不同的是,老人在困惑之后,更加清楚地知道,唯一的路,就是面对自己的生活。那时候,他过年跟着父亲去邻村赶集,买桃酥,过年拜姥姥和舅舅用。他会缠着父亲买鞭炮,他喜欢放鞭炮。他喜欢过年,因为过年可以收压岁钱,那时的压岁钱是五个小铜板。他喜欢吃糖包、吃甘蔗,那时的甘蔗又长又甜。他喜欢打陀螺,村里的井台底下不小心洒了水,结成冰,男孩就在上面打陀螺,女孩则在屋后荡秋千,秋千是用船上的桅杆架起来的……
听这位九十四岁的老人讲述童年往事,像是在听一个遥远的童话。
他也说到了以前的大海。那时的冬天很冷,海都结冰了,他经常从船上踩着冰走到岸上。寒冬腊月,鱼冻在冰里,他把冰块打碎,把鱼捡回去,主要是黑鱼和黄鱼,鱼肉很厚。
“而现在出海的人,把小鱼仔都捕回来了,一网打上几千斤小鱼仔,这叫自己害自己。”从海木匠这里,从老船长的言谈中,我听到了太多这样的质问。有的渔民觉得,海是大家共有的,你不拉网别人也会拉网。当缺少一个严格的共同的行为规范时,还有什么是可以依靠的?其实这也是当下所有行业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不管外部环境如何,关键是你究竟做了什么?承担了什么?看到一些所谓知识分子在大谈特谈宏大问题,而拒绝从个体生命出发承担那些具体事务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可疑的。
眼前这位老人九十四岁了,一日三餐,日常生活,都是自己打理。我问他,作为一个走过了接近一个世纪的老人,独处时经常会想些什么?
老人说,什么也不想。
这个回答过于简单和干脆,完全超出我的预料,我对此有些隐隐的不满和不解。按照我的惯常理解,作为一个年近百岁的老人,经历了那么多的世事,他一定会在独处的时候,逐一回想,感慨万千。不过,这仅仅是我—— 一个所谓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而在眼前这位老人身上,在很多的人那里,并不是这样看待人生和社会的。我的一些所谓思考,不过是一种想象,我一直在想象我和世界和他人之间的关系。其实这是靠不住的。
想到了渔灯。在迷茫的大海上,一个人正当无路可去的时候,眼前突现一盏灯,这是多么让人激动的事。我曾经以为,这是一个关于生存的隐喻。而在渔村亲历的那些人和事彻底纠正了我,告诉我这不是隐喻,这是最真切的现实。
伍尔夫的小说《到灯塔去》,讲述了一个很简单的故事:拉姆齐先生全家和朋友们到海滨别墅去度暑假。拉姆齐夫人答应六岁的小儿子詹姆斯,如果翌日天晴,可乘船去游览矗立在海中岩礁上的灯塔。由于气候不佳,詹姆斯到灯塔去的愿望在那年夏天始终没有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拉姆齐先生和子女重游故地,詹姆斯终于如愿以偿,和父亲、姊妹驾了一叶轻舟到灯塔去。但是岁月流逝,物是人非,拉姆齐夫人早已溘然长逝。
在这部小说中,伍尔夫一定有太多想要表达的东西,却无法完整和准确地表达出来。她选择了意识流。
正如此刻,我想写下对于灯塔的印记,却感到力不从心。
在离开渔村的前一天傍晚,我登上老龙山。我想,是该去看一看那个矗立在老龙山山顶的灯塔了,不管现实中的灯塔是什么样子,我心目中的那个灯塔都已经无法被改变。通往灯塔的山路有些漫长,渔村安排了专人陪我上山。隐在草木间的灯塔,有些荒凉。此前,我一直是远远地看和想象灯塔,现在我来到了灯塔跟前,站在灯塔下看海,看海边的那个渔村,我想起了站在海边遥望灯塔的那些夜晚,心中涌起别样的感慨。我知道我可能再也不会这么近距离地与灯塔相处了。这样的灯塔,在我看来更适合远眺。远远地望着它,就足够了。
眼前一片荒芜,找不到下山的路。我想象若干年前,渔村的人们在山上寻找一条路,只为了点亮灯塔,给渔船指明回家的路。
回家的路如此漫长。
下了山,这次漫长的寻访可以结束了。在渔村的每一个日子里,我都会遥望那座灯塔,却刻意不走到近前,我更想寻找的,是灯塔在渔民心目中的位置,抑或渔民藏在心底的灯塔究竟是什么样子。此刻,这座废弃的灯塔渐渐变得清晰和明朗了。
版权信息